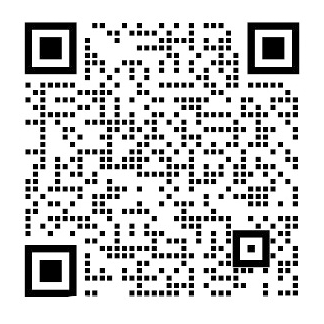教育哲学的前景
原文作者 JONAS F. SOLTIS
单位 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与教育师范学院
哲学最有用的功能之一是提供洞察力。在一个繁忙、复杂、要求苛刻的世界里,我们很少有时间后退一步,去寻找一个能提供全面图景的视角。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从总体上对教育哲学的理念进行哲学思考;不是关于某些特定的哲学,也不是关于我们在教育中的哲学选择范围。我试图提供的观点既有概念性的,也有规范性的。从概念上讲,我将探讨什么是教育哲学的合理描述。规范地说,我将建议教育者应该如何看待教育哲学以实现最大效用,以及专业的教育哲学家应该如何作为专业人士。
在最近的一篇百科全书文章中,我试图通过在个人、公众和专业三个维度上勾勒当代教育哲学的形式,为非专业人士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专业和公共教育哲学的理念。但首先,需要一些背景知识。在下面引用的作品中,我主要关注的是非哲学家在接触专业教育哲学家的当代作品时经常感受到的期望与实际经验之间的不匹配。我想为非哲学家提供一种方式,让他们了解哲学家是关于什么的,并让哲学家们理解那些不在公会的人所提出的真正和合理的需求。
在我看来,对于非哲学家来说,进入这个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似乎是接受一个非常基本和普遍的想法,即拥有一个个人的生活哲学,并将其比作一种教育哲学,一套关于什么是好的、正确的、值得在教育中做的事情的个人信念。我认为,以这种方式对教育进行哲学思考的目的是让个人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个人意义、目的和承诺感,以指导他或她的教育活动。我进一步指出,这对于成为一个深思熟虑的自我指导的教育者,而不是官僚机器上一个没有头脑的齿轮,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这是教育哲学的个人层面,大多数门外汉都希望教育哲学家与之搏斗和写作。然而,很少有实践的教育哲学家以这种个人的方式来写或说教育。一些教育哲学家认为他们有义务帮助未来的教育者发现并形成他们自己的教育哲学,但是许多人认为教育功能是一种过时的遗物,它们遗留在“哲学学派”的方法中,在中世纪的教育哲学中占主导地位。无论如何,我之前的观点是,虽然个人的教育哲学对于有意识和有意义的教育活动非常重要,但经过检查,我们发现当代教育哲学家很少公开参与这种哲学形式,通常在教学中瞄准其他事物还有写作。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公众层面。
从指导个人实践的个人维度看待教育哲学与从公共维度看待教育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旨在指导和指导许多人的实践。任何旨在让他人遵循的教育提案,或任何旨在改变当前教育实践的规范性规定或批评,都存在于公共层面。从柏拉图到杜威,哲学家们一直沿着这个维度运作。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以这种公开的方式对教育持哲学态度,许多人都是,无论他们是记者、政治家、学者、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还是哲学家。公共教育哲学是每个人的事,应该如此。对公共层面的教育持哲学态度的目的在于阐明公众愿望和教育价值观,让合作的公共教育事业具有意义和目的,并为所有认真关注教育的人提供机会,在教育方向上进行深思熟虑的参与。
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教育哲学这一维度的一个方面往往优先于个人和专业领域,教育哲学家应该对公共教育哲学做出连贯而全面的陈述。然而,当代哲学著作往往达不到公众的期望。当然,像杜威、基尔帕特里克和布拉梅尔这样的二十世纪专业哲学家主要是沿着公共维度的缝隙写作的。但许多当代教育哲学家根本没有挖掘出这一特定的缝隙。
此外,最近似乎有更多的非哲学家在他们的工作和著作中被公认为是关于教育的哲学,而不是专业哲学家,例如尼尔《夏山学校》,斯金纳《瓦尔登湖第二》,克里明《公共教育》,古德曼《荒诞的成长》;科佐尔《早逝》;伊利奇,《非学校社会》;科尔伯格,《作为道德教育基础的道德发展阶段》等。因此,教育提案、辩论、批评、计划和政策制定是一个活跃的公共领域,许多人都非常认真、深思熟虑。作为一种人类和社会活动,它在这个术语的最深层意义上是哲学的,尽管所有从事这项活动的人都不是专业哲学家,也不是所有专业哲学家都以这种纲领性的方式从事教育思考。那么,是什么将教育哲学的专业层面与公众区分开来,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这是我将在本文剩余部分探讨的中心主题。
然而,在做这件事之前,有一点需要注意。D.C.Phillips在即将出版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的“教育哲学”条目中指出,可以说,“学术政治和制度化的怪癖”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在学院和大学中只发现了一小部分“专业”教育哲学家,主要是在英语世界,从国际上讲,它们只是更大领域中非常狭窄的一部分。他认为,更好的做法是从更广的角度看待教育哲学领域,将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同行包括在内,而这些同行在其机构中不一定被称为“教育哲学家”。他还声称,像斯金纳和科尔伯格这样的非专业哲学家实际上是在做技术意义上的教育哲学,因此应该包括在任何教育哲学概念中。皮亚杰、维果茨基和乔姆斯基等其他领域的理论家也应该如此,他们的工作与教育哲学有很大的相关性。虽然菲利普斯和我提供了不同的框架,但我们没有达成严重的分歧;所有这些“教育哲学家”都需要以某种方式适应和约会。我们的做法有所不同,但我们都认为有必要对教育哲学进行更广泛、更全面的审视,这可以帮助非哲学家看到哲学与教育事物之间的许多联系。此外,菲利普斯是正确的。实际上自称为“教育哲学家”的人数很少,他们的机构化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在地理上分布很窄。但“专业教育哲学家”确实存在,我认为,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们需要帮助他人更准确地看待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潜在的互惠关系。我最近的很多工作都关注的是期望不匹配的“专业”问题。
我仍然相信,我最初对教育哲学专业层面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基本上,我认为,虽然专业教育哲学既包括个人层面,也包括公共层面,但它增加了自身的层面。专业层面超越了这些主要的哲学对待教育的编程方式,并将专业哲学家的技术工具的方法和使用添加到处理与教育相关的概念性和规范性问题的方式中。当哲学家以专业人士的身份行事时,对教育问题的建议就更少了,而更多的是分析、反思、评估和寻求更清晰的理解。更强调的是确定论点的逻辑合理性、阐明观点的意义、证明价值主张、构建合理论点,以及提供思考教育任务和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从事这种哲学研究时,教育哲学家更倾向于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启发、理解和视角,而不是为教育工作者提供行动方案和政策。
以这种方式进行哲学思考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教育者的概念和规范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哲学上严格的检查、批判、论证、分析和综合论述,使教育事业尽可能理性地自我反思。专业教育哲学家能否做到这一点,直接取决于他们对哲学技能和文学的严格训练和掌握。他们是哲学学者——从事技术性哲学工作的教师,要求严谨、精确,并遵守自己的专业学术准则,就像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和其他学者在写作和教学中所做的那样。
当然,专业哲学家运作的三维个人、公共和职业空间也存在重叠。但也有一种纪律严明、专业化的方式,专业哲学家处理和教育相关的问题,这使它与非专业人士的类似努力不同,非专业人士也可以占据同一空间的一部分。接下来要问的关键问题是,那些占据同一空间的人如何能够以及应该如何相互联系?专业的教育哲学家有义务接触哲学家以外的受众吗?我想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我们教育哲学家有道德义务在公共领域使用我们的特殊技能,就像医生有义务在任何地方帮助病人一样。但为了履行这些义务,我们需要更清楚地了解教育哲学的公共层面的概念,以及我们可能面对的受众和我们可能做的事情。
公共教育哲学有三种意义需要区分,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勾勒出可能的运作模式。第一种是“公开”的观念,即任何希望对教育产生影响的提议或批评都是其本意。显然,个别哲学家或团体可能会以多种方式试图将哲学观点、论据或信息摆在“公众”面前,以及“公开”的许多可能程度。它可以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表达或发表学术论文的方式,让非常少的观众听到或阅读,也可以是通过电视、报纸或其他大众媒体向广大公众传播的重大努力。最后一个例子是马修·利普曼(Matthew Lipman)努力推广他的中学项目“儿童哲学”。
还有第二种教育哲学的“公共政策”意识,在这种意识中,明确的教育政策被塑造、调整、批判和拒绝。在这里,哲学家和其他人就来自官方委员会、委员会、机构等的明确政策开展的合作工作为实现某些目标提供了指导、指示和计划。例如,先发制人、基于绩效的教师教育、业务和能力测试是当代美国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都带有基本的哲学假设或理由。这些不仅是公开的,从公开哲学的角度来说,但同时也是公共的“官方”公共,由一些受到社会认可的机构机构授权或合法化。哲学家可以而且确实是这一决策层面的合作者,但我们都知道,他们中的更多人可以而且应该这样做。他们需要更积极地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公众需要更清楚地看到他们作为具有特殊技能的专业人员所能提供的独特服务。不匹配的期望在这里根本没有帮助。
最后,还有第三种“公共意识形态”,即我们对社会中终身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深层信仰。这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教育价值观和目的,比如我们在美国有意识地承诺利用学校教育提供个人机会和社会流动性,以及我们在学校组织结构中表达的无意识需求,以使人们为我们的技术、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工作条件做好准备。哲学家可以挖掘、审视、批判或试图证明我们的公共意识形态承诺是合理的,无论这些承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或者像杜威那样(可能是公众最期待的,也是每一位职业哲学家最不可能做的),阐明一种新的公共意识形态形式。
这种对教育哲学的公共层面的扩展视角,只为一个可见的专业学者群体提供了一张多途径旅行的粗略地图,这些学者近年来被指责只为自己写作和交谈。然而,在描述这一公共层面时,我并不是在呼吁放弃教育哲学家对自己学术界的基本忠诚。作为职业哲学家,积极的生活和相互之间的互动培养和维持着他们的成长。我还相信,教育哲学家需要哲学的母学科的帮助。但是,还有其他对教育哲学家的发展很重要的专业同事。我们需要与教育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教育工作者和从业者进行实质性接触,以使我们的思想对潜在的相关哲学问题、问题或想法保持开放。事实上,我们对教育所做的一切的相关性必须是我们专业承诺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诚实地称自己为教育哲学家,那就不可能是这样。
因此,虽然我们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受众是我们的哲学家同胞,但我们也有其他两个主要的潜在受众,即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公众。为了有效地接触到他们,我认为我们需要教育他们的期望,以便他们能够将专业哲学家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与他们维持一个实现理想目的的教育体系的需要相匹配。我们还需要能够在不牺牲哲学严谨性的情况下使用公共习语。
上述对公共层面的扩展视角为教育专业哲学家提供了多种方式,通过在更大程度上“公开”、参与公共决策和探索公众的教育意识形态,试图为广大公众服务。但是,关于教育哲学家如何试图接触到其他重要的受众——教育者,我几乎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组:学院、学校或教育部学院、联盟和职前在职从业者。近年来,教育研究人员与在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特殊专长的教育哲学家之间进行了良好而有益的对话。这种“自然”的兴趣重叠应该继续培养,并且不能不帮助为教育研究的概念、方法和结果带来受欢迎和必要的哲学视角。课程开发、管理和教育心理学等专业领域的同事似乎也与具有特殊技术的教育哲学家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对认识论、社会哲学和哲学心理学感兴趣。教育专家和教育专业哲学家的兴趣和关注点之间有着巨大的联系潜力。需要找到办法,在期刊、研讨会、会议上,甚至机构内同事之间非正式地开展有用的、相互激励的对话。双方的理解只能得到改善。
在职前教育层面,专业教育哲学家需要团结一致,达成共识,并提供一个关于教育的哲学视角的核心,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教育工作者职前教育中最基本、最基本的。随着教育哲学专业的发展,书籍、文章、文本以及教授基础课程的方法也在发展。现在是时候重新组合,就基本要素的共同核心达成一致,让多样性和特殊利益随之而来。我认为,这样一个核心应该包括对课程和目标、教学理论、学习和人类发展概念、学校教育和社会再生产以及职业道德的当代哲学观点的实质性处理。当然,哲学家给学生提供的不仅仅是内容。他们尤其擅长教授直率思考的技能,培养对理性的尊重,这两方面对于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学习和培养各个层次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所有这些都应该构成职前教师教育基本哲学组成部分的核心目标。
随着越来越多的在职教师和管理人员被要求或敦促继续他们的专业教育,特殊的机会为直接相关的哲学研究和反思他们作为教育者的意义打开了大门。他们多年的教育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从中筛选思想,寻找有意义的哲学观点。在职前的新手看起来很容易理解,因为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任何能告诉紧张的新手如何去做的事情。众所周知,哲学缺乏实践理论。但是,经验丰富的教师如果已经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从哲学中寻找更广阔的视角、更丰富的理解,以及对自己的教学和作为基本社会制度的教育的更批判性的看法。对于学科教师来说,各种(科学、数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哲学可以为他/她的领域提供令人兴奋的哲学视角。这类研究通常有助于产生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不仅包括内容,还包括“学科结构”对于那些寻求退后一步,将教育视为一项规范的社会事业,可以被批评、改变、引导和重新概念化的经验丰富的教师来说,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史文献,以及当代批评家和其他教育形式的倡议者,可以在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的陪伴下阅读、审查和讨论。对于经验丰富的教师和管理者来说,他们工作和生活在一个需要每天做出影响他人的艰难决定的现实世界中,有必要在哲学家的指导下走到一起,探索职业道德的复杂性和缺陷。
我在本文中试图勾勒出的公共教育哲学和专业教育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但不一定复杂的关系。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或一维的,并不意味着它不容易在任何方向被抓住和穿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希望我提供了视角,并为非哲学家和哲学家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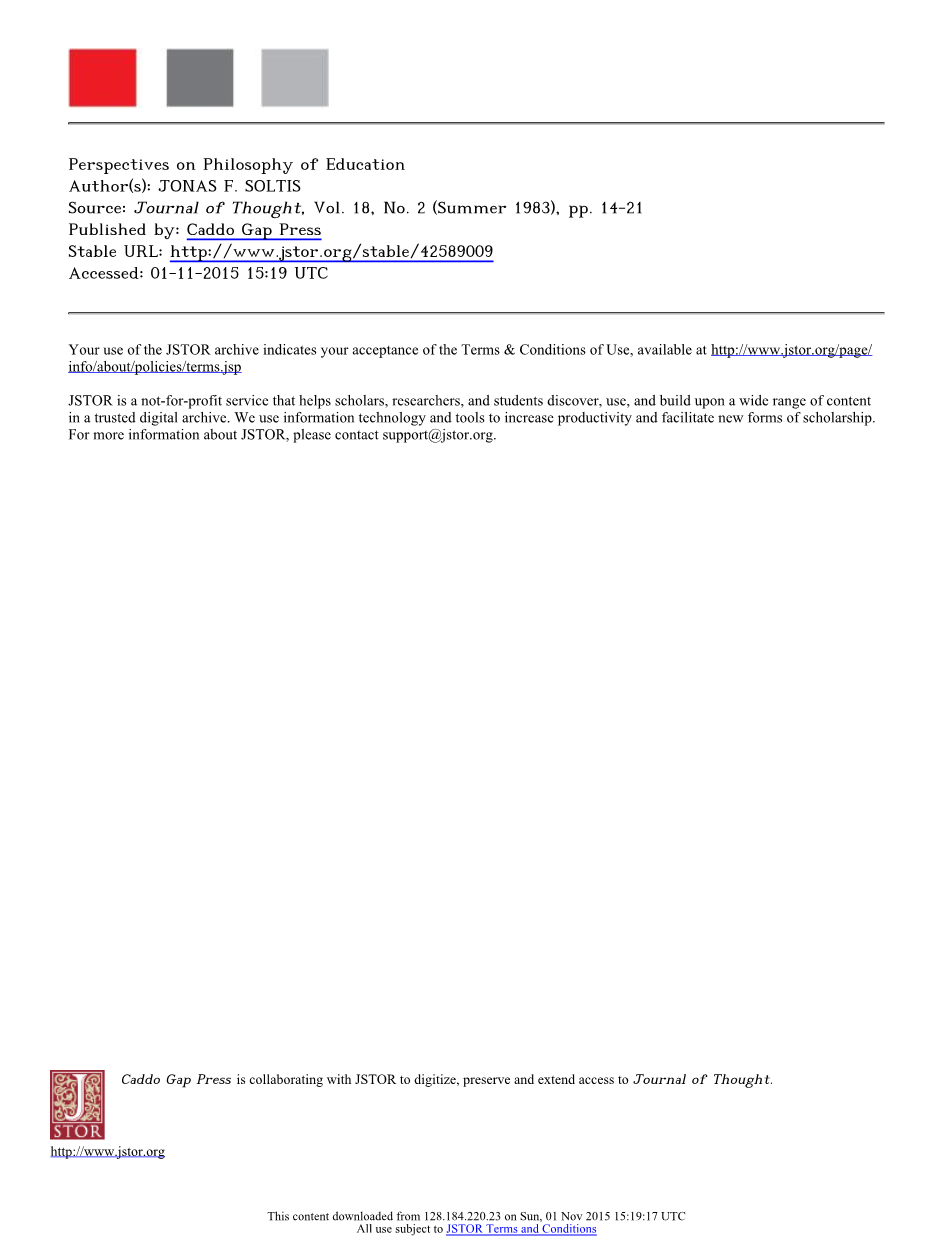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9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4320],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