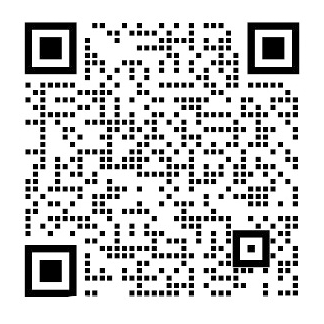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peacebuilding in Nepal
Keshav Kumar Acharya*
School of Behavioral Cognitive an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Armidale, NSW 2350, Australia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wenty-six grass-roots level organizations which is examined by organizational surveys and three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indings show that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are key actor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Nepal and their functions are supportive in reinforcing the peacebuilding process in many ways. First,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ddressing inequality and isolation. Second, its continual practice fosters awareness creation, promote democratic exercise, imparts “voice to the voiceless” and gives clout to the powerless. Third, it inspires the partners to create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mobilizing local resources. Finally, it strengthens the structure of accountability and contributes to peacebuilding. Howeve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practice of governance at the community level was moderate to efficient. Following the discussion of results, this study proposes some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operation of a sound peace process at grass-roots level through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words: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governance; exclusion; peacebuilding; Nepal
Introduction
Peacebuilding is a post-conflict action, predominately a diplomatic course for improv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people (Latifi, 2011). It is a process of cultivating new environments and new cultures which involves obliging contacts between opponents and establishing normalized relations of the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humanitarian kind between ordinary citizens on both sides of a conflict (Reychler, 2006). In a peacebuilding process, a multiple set initiatives from a diverse range of actors including the state, market, civil society/ local citizen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is imperative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s of violence and to protect the people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period of aggression (Ricigliano, 2003). Through these, the root causes of conflicts and violence are addressed, the logical end of conflict is achieved, a strong and legitimate national authority is established, democratic political processes are instituted, responsibility and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are transferred to the new government, the economy is strengthened and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are promoted (Rondinelli amp; Montgomery, 2005). Nevertheless, the conflicting societies to a greater extent are psychologically, physically and materially obstructed by violent forces (Staub, 2012). Such obstructions are positioned robustly in both tangible (killing civilians, destroying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s and damaging bas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intangible (collapsing state institutions, mistrusting in government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manners (Abeysekera, 2011). As a means of addressing both types of impediments in conflict-affected societies, peacebuilding is a “way forward” inventiveness, which fosters reconciliation of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and encourages broader communities to address the conflict agendas through peacebuilding lenses. However, many critics assert that the peacebuilding process is only an outside intervention that has abandoned the real interest and influence groups (Nussbaum amp; Sen, 1993). In Nepal, the notion of peacebuilding has resulted in the settling of armed combat, which was led by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CNM-M) from 1996 to 2006. The politically based armed battle lasted for 10 years, leading to the deaths of an estimated 15,000 people and displacing many thousands more (Robins, 2011). In 2006, the violence stopped after the “12 Points Peace Agreement” was signed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and the Seven Party Alliance (SPA). In 2006, a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PA) was reach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nd the rebellion party, CPN-M. Since that period, the peace process has been operational in the country and various actors have been engaged to uphold a sustainable peace in the society (Bhatta, 2012). Regardless of such enormous initiatives in Nepal, the collapse of the state institutions, social/economic exclusion and the malfunction of governance are familiar characterstics of the society and yielded numerous wicked practices. First, a centralize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inbuilt decision-making system are standard arrangements (Winther-Schmidt, 2011). Second,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from central to bottom has apparently been influenced by elitist bias in that it is not prepared to hear public grievances (Khanal, 2006). Third, limited numbers of people have domination over the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Fourth, an unholy connection between aid agenci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leaders has inhibited the deployment of opportunities to the specific targetgroups. These factors have served to intensify the armed conflict, which ended in 2006. Experiences confirm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the late 1970s forced the neo-liberal policy to be a prominent discourse in development. It has encouraged pluralism,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t has been assumed that access to economic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s increased for all segments of society and that inequality and impartiality in decision-making is reduced.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effective role of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s and operational objectives through structured frameworks, rules, relationships, systems and processes (Orsquo;Mahony amp; Ferraro, 2007). However, it could not promote the genuine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ie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heshire, 2000). In Nepal, it was the realization of formal entry into neo-liberalization in the late 19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尼泊尔的社区治理和建设和平
Keshav Kumar Acharya *
新英格兰大学行为认知与社会科学学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阿米代尔2350
本研究基于对26个基层组织进行的体制分析,并通过组织调查和三个焦点小组讨论进行了检查。调查结果显示,社区组织是尼泊尔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其功能有助于以多种方式加强建设和平进程。首先,它在解决不平等和孤立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它的持续实践促进了意识创造,促进民主运动,赋予“无声者”的声音,并赋予无权者以有力的影响力。第三,它激励合作伙伴创造有利于调动当地资源的环境。最后,它加强了问责制的结构,并有助于建设和平。但是,结果表明,社区一级的治理整体实践适中有效。在对结果进行讨论之后,本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些关于通过社区治理在基层开展健全的和平进程的建议。
关键词:社区组织; 社区治理;排除;建设和平;尼泊尔
介绍
建设和平是一项冲突后行动,主要是改善人们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外交途径(Latifi,2011年)。这是一个培养新环境和新文化的过程,其中包括迫使反对者之间进行接触,并在冲突双方的普通公民之间建立政治,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类型的正常关系(Reychler,2006年)。在建设和平进程中,包括国家,市场,民间社会/当地公民和国际社会在内的各种行动者采取的多项举措对于解决暴力的根源以及在此期间之前,期间和之后保护人民是必要的(Ricigliano,2003)。通过这些措施解决冲突和暴力的根源,实现冲突的逻辑结束,建立强有力的合法国家权力机构,实行民主政治程序,将发展的责任和资源转移到新政府,经济体加强了社会和人力资本(Rondinelli&Montgomery,2005)。然而,冲突的社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暴力的心理,物理和物质阻碍(Staub,2012)。 (Abeysekera,2011)将这些障碍定位在有形的(杀害平民,破坏发展基础设施和破坏基本服务设施)和无形的(崩溃的国家机构,政府中的不信任以及破坏社会关系)方面。作为解决受冲突影响社会中这两种障碍的一种手段,建设和平是一种“前进之路”创造性,促进冲突各方之间的和解,鼓励更广泛的社区通过建设和平来解决冲突议程。然而,许多批评者断言,建设和平进程只是一种外部干预,已经放弃了真正的利益和影响力团体(Nussbaum&Sen,1993)。在尼泊尔,建设和平的概念导致了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分子(CNM-M)从1996年至2006年领导的武装战斗的解决。基于政治的武装战斗持续了10年,导致了估计有15,000人,并且还有数千人迁移(Robins,2011)。 2006年,在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和七党联盟(SPA)签署“12点和平协议”后,暴力停止了。 2006年,尼泊尔政府与叛乱党CPN-M达成了“全面和平协议”(CPA)。自那一时期以来,和平进程在该国开始运作,各种行动者一直致力于维护社会的可持续和平(Bhatta,2012年)。无论尼泊尔采取何种巨大举措,国家机构的崩溃,社会/经济的排斥以及治理失灵都是社会熟悉的特征,并产生了无数邪恶的做法。首先,中央制度结构和内部决策制度是标准安排(Winther-Schmidt,2011)。其次,从中央到下端的决策制度显然受到精英偏见的影响,因为它不准备听取公众的不满(Khanal,2006)。第三,数量有限的人拥有资源和机会。第四,援助机构,官僚机构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不正当联系阻碍了向具体目标群体部署机会。这些因素加剧了2006年结束的武装冲突。经验证实,20世纪70年代后期市场机制的失败迫使新自由主义政策成为发展中的重要话语。它鼓励多元化,竞争和效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直认为社会各阶层都有机会获得经济和政治机会,决策过程中的不平等和公正性减少了。它进一步探讨了正式和非正式机构通过结构化框架,规则,关系,系统和流程实现战略目标和运营目标的有效作用(OMahony&Ferraro,2007)。但是,它不能促进社区真正参与决策过程(Cheshire,2000)。在尼泊尔,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现了正式进入新自由化的进程,这为多个参与者提供了参与发展话语的机会,以应对机构危机,管理体制不善,经济脆弱性和服务提供模糊性。然而,新自由主义对农村社区的否认方式不仅迫使贫困的危机,而且造成贫富差距,推动社会进入战斗的峡谷。从这个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偏好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社区的福利,这使得社区在建立社会安全网时失去了功能(Cheshire&Lawrence,2005)。尽管尼泊尔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Panchayat系统下的基层治理方面做出了努力,但Panchayats仍然大部分是中央政府的延伸,主要集中驱动,很少强调加强地方治理。 1990年,尼泊尔实行民主制,1951年实行民主制,这为民众在宏观层面改善国民经济和政府行为带来了一些希望和愿望,同时促进了惠及贫困人口和其他各种被排斥或微观层面的边缘化部分。经验表明,尼泊尔社区在社区内实行管理制度,鼓励当地人参与社区计划制定,咨询和资源管理的制定。在这种背景下,社区治理赋予社区权力和控制权,使公民,政府和非政府可以共同行动制定和实施政策,建立网络和联系,设计社区一级的角色和责任(Somerville,2005年)。通过这些过程,社区治理在赋予人们权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他们提供公民“声音”,刺激民主并提高他们制定解决冲突战略的效率(Taylor,Braveman,&Hammel,2004年)。尽管如此,尼泊尔基层治理体系面临风险的原因有几个。首先,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精英统治导致了低水平的公众参与。这使强大的人能够从权力结构中的垄断中受益。其次,实现社区治理及其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否认,因为它们被滥用或操纵(Kavada,2010)。尼泊尔建设和平进程的主要不足在于新自由主义议程,该议程不仅激励建设和平行动者根据“放松管制,非国籍化和私有化”框架设计其模式,而且还限制了基层代表性建设和平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尼泊尔的建设和平进程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尽管政府和供资机构高度重视。因此,本研究考察了社区治理的贡献,这是加强地方社区,促进建设和平进程和获得地方一级建设和平活动所有权的主要机构,以促进尼泊尔的建设和平进程。
文献回顾与理论
二战后,出现了许多结构和多元理论,强调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为国家控制国家经济提供了更多的行政和立法权力(Pankaj,2007)。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许多限制,导致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地区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失败。 Kohli(2004)指出,非洲的新世代关系,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模式以及亚洲部门的殖民地建立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失败的原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通过新自由化达成了共识,以解决国家失败,并通过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和加强私营部门的作用来恢复国家经济增长(Kotz,2002)。与此同时,“第三次浪潮”民主通过权力来源为现有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亨廷顿,1991年)。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循环被扭转,这对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正义,社会凝聚力和地方民主的保留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导致大部分社会不仅在结构上有障碍工作,并且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上保持持续,而且导致公共服务的“剥离”,结果许多社会由于失业和社会因此而分裂并受到威胁排除(Campbell,2001)。当代建设和平的做法似乎植根于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相同的错误假设(巴黎,2010年)。针对这种误解,政策制定者,从业人员和学者纷纷转向系统和结构的治理。一些作者认为治理是从“政府到可治理”的范式转变(Howlett,Rayner和Tollefson,2009; OToole&Burdess,2004)。治理是与权力和绩效以及规则和反应相关的治理行为。这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激励和自我调节的国家和非国家进程。
社会和国家为管理有效的公共服务而行使的组织,独立的司法体系,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和公共基金以及多元化的制度结构(Rhodes,1996)。然而,尼泊尔的政府,非政府机构和捐助者不愿意在他们的行动和方法上支持治理(Dahal,2012)。治理变弱的趋势证实,2011年尼泊尔在182个国家中的腐败排名是第154位,而2010年在178个国家中位列第146位。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个机构“和平基金”分析了该指数全球177个国家的失败国家,并指出,尼泊尔的排名在2009年仍然排名第25位,2010年排名第26位(Graner,2001年)。相比之下,尼泊尔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7/08年度人类发展指数(HDI)为0.534,2006年为0.509,2001年为0.471(UNDP / N,2009)。这些表明,治理处于弱势地位,机构和程序薄弱,发展方案缺乏所有权,资源管理不善以及未能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经验指出,一些因素是治理弱化的原因。首先是分封权力结构,由封建精英担当。其次,不合理的发展模式集中在为政治有益的发展项目分配更多的资源,而忽视当地的议程和社会背景。第三,强加于发展话语的政策干预忽略了土着知识(Metz,1995)。此外,尼泊尔社会的特点是封建制度,民族多样化和复杂的权力结构(Dahal,2012)。这种结构性限制使政治和社会压迫和官僚不诚实感受到了影响。在Panchayat时期,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的共同理念得到充实,具有尼泊尔语,文化和服装等独特的民族特征,接受印度教为国教,国王为统一的象征。原则上,这种意识形态压制和排斥人民;那些在社会,经济和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然而,当政府在1963年制定了一份法律文件“Muluki Ain”时,努力取消压制和排斥的情绪。然而,执法不力,政府不诚实和Panchayati精英对政治制度的统治导致它无效。尽管1990年恢复民主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希望和希望,但由于政治不稳定,治理失误和资源分配不均等混乱模式,国民经济和政府行为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人们的期望(Kumar,2005年) 。经验证实,当尼共(毛派)将资本化并明确了现有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时,它开始通过向政府提出“40点要求”来反对该制度。后来,CPN-M在这个“40点需求”的基础上宣布了“人民战争”。
但是,尼共(毛派)的中心要求是用世俗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取代君主制。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战争”于1996年宣布,并于2006年结束,扰乱了社区的社会资本,并导致基层发展进程的崩溃(Upadhayaya,Muuml;ller-Bouml;ker和Sharma,2011)。社区可以通过参与成员,测量结果和实现行为结果,在社区治理体系下获得信心。这构成了一个社区管理系统,帮助社区作出重要决定并帮助他们从底层处理和平进程(Gaynor,2013年)。一些作者认为,这是20世纪后期的新干预(Armstrong,Francis,&Totikidis,2005),它鼓励集权和权力下放到当地层面,赋予当地社区权力以缓解当地的争端和稀缺性Avis,2009)。它象征着一些规范性价值观,如复杂社会中基于网络的协作和协调,自治,公众参与和民主创新(Stoker,1998)。布莱尔(2000)指出,社区治理以多种方式创造了一个自愿参与少数民族群体的环境,如妇女,穷人和边缘农民。首先,鼓励穷人建立自己的组织,并寻求国家和更广泛的民间社会的支持。这些组织一旦建立起来,就可以影响地方和中央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其次,它确保以参与和协作的方式提供有效的服务(Gaventa,2004)。 OToole(2006)认为,社区可能已经存在机构真空,因此当地居民可以通过社区协会参与社区治理活动,从而有可能创建更加强化的社区治理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区治理成为一种“社区运动”,强调了当地社区内的权力分配多元化以及与市场社会中的公民空间的联系力量(Turner,2012)。现在许多基于社区的组织(CBO)正在出现。这些重点放在包容性决策制度,充足的谈判能力,经济和社会安全以及社区赋权(Opare,2007)。社区组织在建设和平进程中作为潜在的合作伙伴是很有希望的。他们是最真实可行的组织,拥有丰富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基层治理问题方面的工作。基层社区组织的发展配备了可以被描述为社区治理的地方自治系统,从政府的概念转向治理(OToole&Burdess,2004)。一种超越政府的灵活方法对于在社区一级有效和以公平为基础的资源分配至关重要。首先,它在解决不平等,孤立和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Chaskin,2001)。其次,它促进意识的创造,民主
运动,社区建设,宣传和协调,联系和网络发展。第三,它有助于动员当地资源(Chapagain&Banjade,2009),而第四,它为“无声者”提供了声音,并对无权者产生了影响。最后,它加强了问责制的结构并促进了权力下放(Acharya,2010)。在尼泊尔,作为基层服务提供者的主要参与者,社区组织的出现,显示了贫富差距的显着性,并促成了社会的凝聚力和民主性。最初,Guthis,Rodis,BhejasandBhajans Kirtan团体等社区组织的职能承担了社会和经济基层活动(Bhattachan,2002)。然而,20世纪50年代早期通过旨在改善农村生计的Tribhuvan Gram Vikas项目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尼泊尔社区组织活动的正式化过程(Shrestha,2004)。到70年代初,CBO的数量增加了,捐助者开始强调CBO在发展中的作用(Dhakal,2007)。小型农民发展计划(SFDP),生产性贷款发展计划(PLDP)和其他区域相关计划已在尼泊尔的外部支持下实施为主要的由社区组织主导的倡议。在这个框架下,社区治理体系在公共和社区话语中越来越受欢迎,这使社区参与者能够通过社会内部的结构化框架和程序实现战略目标和运营目标。尼泊尔的社区治理制度正式实现是在1989年制定林业总体规划后制定的(Kanel&Dahal,2008)。这大大鼓励了社区参与决策,包括当地森林资源的管理。在这种背景下,社区治理鼓励地方行为者,主要是社区及其组织,有效履行其职责,加强内部和外部能力,开展合作以提高服务质量。另外,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自力更生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326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居住地区和基本生活条件对 50 岁以上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和诊断经验的影响——使用韩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数据进行评估外文翻译资料
- 基于混合方法研究的秘鲁亚马逊地区妇幼保健卫生服务利用相关观点和健康寻求行为分析外文翻译资料
-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外文翻译资料
- 日本男大学生生活方式因素与骨密度的关系外文翻译资料
- 健康素养与生命质量之间的关系: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外文翻译资料
- 2型糖尿病的流行病学、风险因素和预防的发展趋势:综述外文翻译资料
- 大学生的食品成瘾与生活方式习惯外文翻译资料
- 高血压患者疾病知识、药物治疗及相关药物依从性水平外文翻译资料
- 波兰孕妇分娩恐惧的相关因素外文翻译资料
- 2020年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吉马的吉马医疗中心参加产前保健的孕妇的睡眠质量和相关因素:横断面研究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