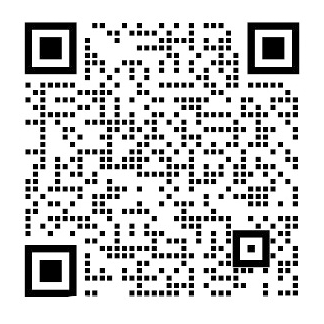肿瘤耐药性的研究进展
原文作者 Neil Vasan, Joseacute; Baselga amp; David M. Hyman
单位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摘要:癌症耐药性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们采用还原归纳的方法来定义和分离耐药性的关键决定因素,包括肿瘤负荷和生长动力学;肿瘤异质性;物理障碍;免疫系统和微环境;无法治愈的癌症驱动因素;以及施加治疗压力的许多后果。我们提出了四种针对耐药性的通用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基于对肿瘤的早期检测,从而可以拦截癌症;治疗期间的适应性监测;添加新药和改进的药理原理,从而产生更深层次的反应;以及通过高通量合成致死率筛选、临床基因组数据和计算建模的整合来识别癌细胞的依赖性。
耐药性仍然是癌症患者治愈的主要限制因素。癌症中的耐药性问题与传染病领域有很强的相似性,因为这两个学科都受到高度增殖的内在或外在侵略者的挑战。与抗微生物治疗一样,早期化疗药物(如氮芥[1]和氨基蝶呤[2])的初步成功所带来的兴奋很快被证据表明,尽管肿瘤迅速进入缓解期,但它们产生了耐药性,导致疾病复发。
对单药化疗耐药问题的初步解决方案——联合给药具有非重叠作用机制的药物或多化学疗法,来自抗菌治疗的规则手册[3]。这种经验方法在某些形式的淋巴瘤、乳腺癌和睾丸癌中非常有效[4-6]。因此,联合化疗成为癌症治疗的新范式,导致开发出越来越复杂的方案。此外,许多不同的剂量强度方法,包括较短间隔的化疗或更高剂量的化疗用生长因子支持来防止持续的骨髓抑制[8,9],通过防止肿瘤的早期再生,提高了这些疗法的成功率。在世纪之交,也就是在引入近50年后,多化学疗法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趋于平稳。手术、放疗和综合化疗显然不足以治愈许多类型的肿瘤。
因此,针对将正常细胞和组织转化为恶性肿瘤的关键使能特征和获得能力的新治疗策略开始开发[10,11]。引入破坏这些标志性特征的疗法,包括靶向疗法,是一个重要的飞跃。事实上,对癌症生物学决定因素的理解已经导致针对酪氨酸激酶、核受体和其他分子靶标的高效疗法。雌激素受体 (ER) 和雄激素受体 (AR) 拮抗剂以及 BCR-ABL、HER2 和 EGFR 抑制剂的初步成功导致了开发针对癌基因和其他关键细胞脆弱性的药物的巨大努力。最近,通过使用免疫学方法识别和攻击癌症,肿瘤治疗再次取得进展。抗 CTLA4 [12] 和抗 PD-1/PD-L1 [13]使适应性免疫系统的负调节因子或检查点失效的单克隆抗体在多种肿瘤类型中产生了显着的抗肿瘤活性,甚至治愈了。然而,与之前在常规化疗中观察到的情况类似,最终对靶向和免疫疗法的耐药性仍然是常态[14]。这就是癌症和传染病之间的相似之处可能不同的地方:例如,联合治疗常常导致疾病在 HIV 中检测不到或在结核病中治愈,但在转移性癌症中,这是例外而不是规则[15]。不出所料,癌症似乎是一个更复杂的生物学问题。
在这里,我们试图通过列举耐药性的基本决定因素并考虑它们对开发成功治疗策略的影响,提出一个概念化癌症耐药性的框架。这些耐药性的基本决定因素在癌症历史上以独特的迭代出现,导致不同的临床状态,从极端敏感到对治疗完全耐药。我们描述了针对这些决定因床状态,从极端敏感到对治疗完全耐药。我们描述了针对这些决定因素的标准和新兴干预措施,并考虑如何将新技术和药理学进步与这些干预措施相结合,以预防、延迟或恢复对治疗的抵抗。
耐药性的生物决定因素
就其最简单的定义而言,癌症治疗是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系统:(i) 治疗;靶向 (ii) 癌细胞群;在(iii) 特定的宿主环境。该疗法的药理特性,连同癌细胞的内在和获得性物理和分子参数以及外在环境因素,导致了临床反应的范围。许多关于癌症耐药性的描述都集中在固有耐药性和获得性耐药性之间的二元差异上。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这些因素的重叠组合,许多肿瘤具有或变得具有抗性。我们建议,在定义耐药性的基本生物学原理时,可以创建一个框架来理解对现有和未来疗法的耐药性(图 1a)。我们相信,通过将癌症和临床科学的重点分别放在解决每个决定因素上,可以管理耐药性问题(图 1b)。
图1:理解耐药性的框架
- 耐药性的生物学决定因素。肿瘤是异质的,位于包含基底膜、脉管系统、免疫细胞和肿瘤微环境等组成部分的环境中。肿瘤的物理参数、基因组和周围环境的变化驱动耐药性。b,管理耐药性生物决定因素的护理标准和新兴方法。许多临床诊断和治疗策略可以针对耐药性的决定因素。
肿瘤负荷和生长动力学
肿瘤负荷和可治愈性之间几乎具有普遍的相关性[16]。在许多肿瘤类型中,诊断时的肿瘤大小(或细胞数量,在液体肿瘤的情况下)可能是最常用于估计预后的变量;较大的肿瘤与增加的转移风险相关[17]。在化疗初期,并未完全预料到这种大小和可治愈性之间的负相关。早期的数学模型,例如“对数杀伤”假设,提出联合多种药物在多个周期内单独杀死对数部分的细胞将允许肿瘤负荷连续减少,直到疾病完全根除。这在对化疗高度敏感的肿瘤中是正确的,例如一些淋巴瘤和生殖细胞肿瘤,但不适用于许多其他癌症类型。
为了更准确地模拟癌症生长,提出了Goldie-Coldman假说[19]。这个模型是由精液微生物学实验提供的,它考虑了肿瘤的大小,也包含了耐药性的出现。根据这个假设,癌症包含耐药克隆的概率取决于突变率和肿瘤的大小[20]。事实上,给定一定的突变率,大小成为预测耐药突变存在的关键决定因素。该模型衍生出多个概念,包括交替使用非交叉耐药的化疗组合,而不是一次给予所有治疗(通常受毒性限制),与序贯治疗相比,在预防耐药性方面更胜一筹。治疗顺序的交替将允许肿瘤在更早的时间点接触更多的总药物。这一假设在临床实践中并未得到一致证实,这表明需要考虑其他复杂性[21]。
此外,尽管肿瘤大小是耐药性的关键决定因素,但肿瘤生长速度和治疗引起的生长动力学变化也在治疗反应和耐药性中起关键作用[22]。肿瘤生长动力学变化很大,从惰性到侵袭性不等。尽管生长率低的肿瘤通常与长期生存相关,但它们通常无法通过细胞毒性化疗甚至靶向治疗治愈。相比之下,以更高速度生长的肿瘤可能对化疗非常敏感。生长速度和肿瘤大小之间也有直接关系,这解释了例如筛查计划中间隔癌症病例的频率[23]。
或许最能解释癌症生长及其治疗后消退的模型是诺顿-西蒙假设。该模型适用于大多数实体瘤,基于Gompertzian生长曲线。根据该模型,肿瘤以sigmoid方式生长[8,25,26]——在低肿瘤负荷下呈指数增长,随后随着它们达到更大的尺寸而以较慢的生长速度接近平台。因为药物会减小肿瘤的大小,所以它们会影响生长动力学。单次化疗后,剩余的肿瘤部分可能会恢复其指数增长的早期阶段。按照这个逻辑,通过防止两次治疗之间肿瘤的快速再生,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根除率。这导致了剂量密集化疗的概念,这种方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间隔内给予最有效的药物剂量水平。剂量密度概念的临床证据已在早期乳腺癌和卵巢癌中得到证实,在特定情况下,更频繁地进行化疗可提高总体生存率。剂量密集的方法不足以将无效的疗法转化为有效的疗法,而是已被用于提高已建立方法的功效。与化疗相比,靶向治疗中剂量安排的作用受到的关注较少,我们建议这可能是一种加深反应和增加治愈率的策略。
肿瘤异质性
癌症异质性可能是最容易概念化的耐药性原因[27]。癌细胞通过产生空间和时间遗传多样性的各种突变过程获得基因组改变[28]。这些过程以不同的进化速度发生——从与年龄相关的突变速度相对较慢,到 APOBEC 酶对基因的频繁编辑(一个在肿瘤进化过程中增加的过程),再到诱发的戏剧性和灾难性事件的爆发。通过基因组不稳定性[29]、染色体碎裂[30]和染色体不稳定性[31]。大的染色体改变可以被视为宏观进化事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代表耐药性发展的不归路,说明早期治疗干预的重要性。与生态系统选择压力一起,突变过程导致平行和趋同进化,以及原发和转移部位克隆的空间隔离[32]。这些压力包括外源性暴露、内部环境动态和癌症治疗本身。选择性治疗压力的影响已经得到很好的表征,范围从靶向细胞克隆的消失,到新的耐药突变的获得,到信号和表观遗传学的适应性反应,最后是肿瘤表型的完全改变[33]。在某些情况下,治疗(主要是化疗)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相当于诱导基因组不稳定状态。例如,在低级别胶质瘤中,替莫唑胺化疗会导致复发时的超突变肿瘤,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肿瘤转变为高度侵袭性的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34]。同样,克隆性造血——造血干细胞中白血病相关基因的反复体细胞突变证明——与先前接受过放疗和化疗有关,并增加了患白血病的风险[35]。这些观察结果应促使我们仔细权衡实施化疗或放疗的潜在意外后果。
一个关键的临床问题是如何测量肿瘤异质性。目前,异质性是通过对诊断时存档的肿瘤样本或随后复发时的活检肿瘤样本进行基因组测序来评估的。这种做法,尽管它在某些情况下有用的治疗选择 [36]都具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是不可能准确地捕获肿瘤异质性,与癌症治疗产生明显的影响。例如,靶向“可操作”的驱动突变可能只有在突变是截断性的(即克隆性的,并且在其一生中存在于肿瘤的大多数亚克隆和区域中[37])时才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在其他情况下,发现给定的突变可能并不能保证该突变是克隆性的。相反,突变的稀少并不能保证它是偶然的。事实上,ESR1[38]和PI3K 通路基因[39]中的亚克隆驱动突变足以驱动对靶向治疗的抗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驱动突变的“克隆性”目录可能会提供信息。
物理障碍
癌细胞可以在肿瘤内产生空间梯度,阻止足够的血流,从而产生促肿瘤发生的缺氧环境并减少肿瘤对药物的有效暴露。尽管减少流向肿瘤的血流是抗血管生成剂的一种已知作用机制[40],但这可能不是完整的故事。替代证据表明,抗血管生成药物也可以使血管结构和功能正常化,促进全身药物的递送,例如化疗甚至靶向治疗[41]。最近,抗血管生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抗 PD-1/PD-L1 抗体的组合也证明了似乎具有协同作用[42,43],尽管这种临床观察背后的确切机制尚不确定。
癌细胞可能在“避难所”或全身给药的药物未达到治疗浓度的解剖空间中定殖和增殖。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中枢神经系统 (CNS) 和血脑屏障[44]施加的物理边界。额外的庇护所包括腹膜(可以通过腹腔内化疗)和睾丸,这导致对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儿童进行预防性放疗[45]。在这些避难所中,CNS 可能代表了最高的未满足的医疗需求。一些肿瘤类型,例如肺癌、HER2 阳性乳腺癌、黑色素瘤和肾癌,具有特别高水平的 CNS 趋向性。各种方法都试图解决这一艰巨的临床挑战,包括改进的放射治疗技术,允许更有选择性地靶向大脑中的肿瘤,以及穿透血脑屏障的靶向治疗。与单独的立体定向放射外科相比[46],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立体定向放射外科联合治疗的早期研究显示出在诱导每个病变快速和完全反应方面的前景。这些数据表明,结合局部治疗和全身检查点抑制来攻击宏观脑转移可能是控制 CNS 转移的一种有前途的方法。最终,中枢神经系统侵袭的解决方案并不明显,但我们开始深入了解导致迁移穿过血脑屏障的潜在机制,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趋向性和生长[47-49],这可能转化为治疗方法。
免疫系统与肿瘤微环境
肿瘤微环境——由免疫细胞、基质和脉管系统组成的周围空间——可能通过多种机制介导耐药性,包括阻止肿瘤细胞的免疫清除、阻碍药物吸收和刺激旁分泌生长因子以发出癌细胞生长的信号[50]。
检查点阻断免疫疗法的成功强调了肿瘤逃避免疫的重要性,这导致对晚期黑色素瘤、肾细胞癌、非小细胞肺癌(NSCLC)、尿路上皮癌的疾病的持续长期控制和微卫星不稳定癌症等。一些免疫治疗耐药的肿瘤具有低突变负荷,这导致可用于呈现的新抗原缺乏,并最终阻止识[51,52]。已经阐明了对检查点阻断的一些抗性机制,包括 beta;2-微球蛋白(削弱肿瘤抗原呈递)和JAK1或JAK2的缺失突变(使肿瘤细胞对干扰素gamma;不敏感)[53]。
免疫抑制性癌症微环境——所谓的“免疫沙漠”——现在被认为是检查点抑制剂的主要障碍,因为存在调节性 T 细胞、骨髓源性抑制细胞、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所有这些可以抑制免疫介导的抗肿瘤作用。这导致了对一系列技术的研究,通过招募免疫效应物将免疫“冷”肿瘤转变为“热”肿瘤[54]。这些技术将检查点阻断与抗血管生成剂、靶向治疗、代谢调节剂、溶瘤病毒、表观遗传疗法和其他检查点结合起来。
不可治疗的基因组驱动因素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英语原文共 11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8117],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β-榄香烯和西妥昔单抗联合治疗通过诱导铁死亡和抑制上皮间质转化对 KRAS 突变的结直肠癌细胞敏感外文翻译资料
- 介孔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进展外文翻译资料
- 负载姜黄素聚乙二醇化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用于光动力治疗的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探索介孔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在新型药物给药系统开发中的作用外文翻译资料
- 基于聚天青A-铂的高灵敏度H2O2传感器沉积在活化丝网印刷碳上的纳米颗粒电极外文翻译资料
- 用于过氧化氢分解的大比表面积多孔MnO2-CNT催化剂外文翻译资料
- ONPATTRO (patisiran)脂质复合注射剂,静脉使用的处方信息外文翻译资料
- 肿瘤耐药性的研究进展外文翻译资料
- 癌症治疗中mRNA前体剪接的小分子调节剂外文翻译资料
- 在大肠癌和黑色素瘤的斑马鱼异种移植模型中,来自硫丹单 抗的凝集素有效抑制血管生成和肿瘤发展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