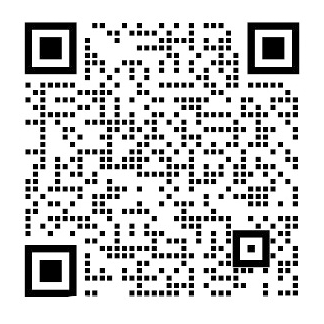集体无意识的反思:荣格在当代心理学和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原型想象
原文作者:Harry T. Hunt
摘要:荣格与当代人文科学之间需要的和解,或许更少地停留在一个生物学家集体无意识中备受争议的关联性上,而不是像荣格心理学的现象学和经验核心那样,重新描绘出一个原型想象。在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面,这方面最有前途的方法来自于结合隐喻和通感的认知心理学、想象吸收的个体差异。
一、引言
作为一个在阅读荣格心理学着作的基础上进入学术心理学的人(亨特1989,1995a,2003),我只能认为荣格心理学被越来越多的心理学教材和人格课程所排斥是深深的不幸。同时,经过培训的荣格临床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界的一致学术研究往往被拒之门外,这与医患对话的独特个性不相干,尤其是沙姆达萨尼详细论证了荣格本人试图将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经验与当时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努力。
接下来,我将主要关注荣格对神话、宗教等现象的描写集中,以及我认为是其心理学的经验核心的那种用于个体儿童和成人发展的光辉经验原型意象。这个核心和最近在不同领域的研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一致性:
- 隐喻的认知心理学;
- 想象吸收的个体差异,作为对鲜活的梦、创造力和超个人意识状态开放的预测;
- 灵性作为情绪智力的高级形式;
- 萨满教与神话思维的人类学;
- 意识社会学本身已经内在地具有集体性质。
本文的一个主要焦点将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中的一些关键矛盾和紧张关系,这种集体无意识可以使它逐渐与这些其他支持学术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概念格格不入。同时,也有相应的方法来重新描述荣格的心理学,这些方法已经隐含在荣格本人的着作中,显示出它与这些发展的更深层次的共鸣。
这里不那么中心的将既有近期试图展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与当代进化生物学发展的一致性,也有众多后现代解释学对荣格的重新解读。关于前者,虽然肯定有趣的是,荣格后来对集体无意识的提法与先天行为的神经科学、鲍德温效应和自组织系统方法在多方面表现为一致,都不清楚演化理论,不管是荣格自己的理论还是最近的理论,如何在原型想象和光明体验的经验现象中,与希尔曼和科贝特所认为的荣格心理学的经验核心有直接的逻辑或演绎联系。的确,这些与当代隐喻和想象研究(亨特1995a)高度吻合的现象,似乎与一些截然不同的演化宏观模型同样一致。同时,对荣格的纯粹解释学方法,虽然毫无疑问地在临床和哲学语境中解放出来,但往往伴随而来的是对任何与“实证主义”人文科学相关的问题的驳斥。这只会增加他们与学术界的隔阂,与荣格本人对苏黎世训练研究所原创成立后继续实证研究的希望不符。
二、荣格集体无意识中的矛盾及其在隐喻认知-发展心理学中的潜在消解
荣格无论在早年(1912)还是晚年(1954)对集体无意识的定义,都在神话中会造成跨文化的共性,以及以世界宗教为核心的光辉经验的形式包含着一种隐含的冲突和概念上的张力。一方面,原型想象是意象创造力和精神发展的源泉。荣格(1912)明确指出,它本身并不是徒劳的或幼稚的,而是一种积极的、成人的发展。从而荣格预料到认知心理学对多种形式的符号智力的进路,以及最近对一种lsquo;精神智力rsquo;的讨论(下文)。
另一方面,原型体验感觉像是对起源和来源的回归。深深融合的光辉经历会让人觉得这两种经历都是全新的,好像它们一直都是以某种方式被人知晓。一个人怀疑荣格is在这里受到柏拉图和普洛蒂纳的观点的指导,认为深刻的直觉洞察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忆”。但是荣格也遵循他自己一天的进化模式(沙姆达萨尼2003),提出一种系统发育,祖先,有时'种族'无意识,包含人类进化的'古老遗迹',以解释这些跨文化相似性的'回忆'或复兴。因此,原型想象同时是一种更高的'精神智能'(使用当前的一些术语)和生物本源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潜在的矛盾?荣格(1934,1951)常常明确表示,他正在发展新柏拉图主义和不可知论主义的自然主义心理学版本,作为现代深度心理学最接近的西方祖先。举例来说,在这些传统中,沉思冥想既是灵魂的更高的个体觉醒,也是一种回忆,是回到从神性创造中走下坡路的起源。但一旦我们用一种现代的、大致达尔文式的进化论视角来代替传统的自上而下的lsquo;存在的大链rsquo;,来源或起源就不再是lsquo;更高rsquo;和神性的,而是lsquo;更低rsquo;和原始性的——离开荣格去寻找lsquo;向下rsquo;进入人类进化的更原始的阶段,以定位光辉经验的原型形式。因此,随着现代性的范式转换,原型想象既是一种更高的特异性的人类发展,也是一种向系统发育共性的铸造。在个体发展中,这种隐含的矛盾成为可能被称为'浪漫困境'的问题,福特汉姆(1958年)和最近的梅奇恩特(2006年)将通过重新整合和/或隐喻性地阐述早期的对象关系或情感模式,建立一个特定成人自我实现过程的模型。
荣格本人有选择地意识到这种更高/更低的张力,特别是后来对其潜在的拉马克式含义的质疑以及种族差异也被理解为最终生物和遗传的可能性。有时,而且更有可能的是,荣格(1934)绕开了生物起源的问题,简单地说,只有在所有民族中都存在lsquo;共同的大脑模式rsquo;的程度上,才可能存在集体的无意识。然而,在我们这个神经科学迅速发展的时代,lsquo;共同的大脑模式rsquo;必然导致更关键的问题,lsquo;是的,但又是什么样的?rsquo;。
这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一种是源于原始起源的进化下降模式,另一种是个体灵魂的更高沉思上升模式。一方面,史蒂文斯(1982,2003)的工作将原型想象理解为系统发育原始皮层的激活,包括边缘区和上脑干的丘脑-后脑系统。这种方法依赖于麦克兰(1973)提出的大脑三体进化层次的概念——具有较低的爬行动力层和支持人类新皮质的哺乳动物初级影响区。这与格罗夫(1980)等精神药物研究者强调原型状态下动物意象的动机强度和突显性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还有詹姆斯·希尔曼的(1975);库格勒和希尔曼(1985)将原型经验重新描绘成一种lsquo;自主的、基于隐喻的想象rsquo;,详细阐述了后来荣格对炼金术的分析,其中的lsquo;心理学家rsquo;原型在一种合成主义中介的想象中把心智和物理本质联系在一起,以物理隐喻的优先性为基础:
对于某些敏感的人来说,通感不仅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怪癖,因为他们的数字是颜色,颜色是舌头上的味道,或者音乐的音调是几何形式。通感——一种感官与另一种感官的相互渗透——在我们想象说话的共同话中一直在进行。显然,通感就是想象的方式。
在这种方式上,地球、空气、火、水的跨模态感官品质以及动植物的多重特征成为自我指称或自我象征隐喻的外化来源。而史蒂文斯和荣格有时倾向于将原型动物意象字面化,希尔曼和人类学家欧文斯(下文)则将它们看作是折叠在部落神话系统中的具有表现力的感官载体,认为它们是强烈而具体的人类感受状态的语义标记。在认知心理学中,莱考夫和约翰逊(1999)也发现了类似的跨模态的'意象图式'(容器、路径、中心、力量等),它不仅是所有思想的基础,而且似乎是完全成人感觉的内在形式——如'加热'、'流淌'、'沸腾'、'爆炸'等不同的愤怒感。这些已经外化于自然的隐喻也将是广义的跨文化的,但独立于任何特定的植物学或祖先的心灵。
这样一种想象——合成性的、创造性的隐喻性的、独特的人类——最有可能位于新皮层的右顶叶区域,最近的神经科学确实把成人的合成性经验和新颖的隐喻思维都定位在那里。这种最近对荣格集体无意识更高想象力一面的确认,与本质上无法研究的系统发育无意识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与原型想象的经验现象的联系无论如何总是更为遥远和推测。
在这种方式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最直接地定义了一种象征性认知。在哲学上,这与新康德试图识别多元智能的不同“先验”是最一致的,如皮蒂卡宁试图根据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重新解释原型。在社会文化方面,它可以与涂尔干(1912)的'集体意识'概念相提并论。涂尔干最明显地理解为神话、仪式和宗教的'集体表征'。这种“集体意识”的思想一旦在拉科夫和约翰逊的“意象图式”中加入了原型想象的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基层,就会承担起跨文化的成分———同样嵌入在肉体和动物性的表达模式之中,并因此不断地作为隐喻的外化来源而获得。在这里,杜尔克海姆的'集体意识'成为了与梁启超'集体无意识'的操作对等物。因此,皮蒂卡宁(1998b)在与史蒂文斯(1998)的辩论中,很快放弃了他对原型原型的社会文化分析中的跨文化共同性问题,因为这种共同性也会遵循物理隐喻的经验普遍性。
在心理学中,这种认知方式也可以看作是加德纳(1983)对多元智能的延伸,包括语言的、逻辑的—数学的、空间的,而且——与现在的讨论最相关——他所说的lsquo;个人智能rsquo;、个人内部和个人外部。在这里,如果超个人或外向的一方最大限度的成人发展构成了政治智能(加德纳1996),我们可以认为,其更内向的一方完全成熟的潜在成人发展可以被视为一种精神智能,这一观点已经与荣格(1921)在《心理类型》中的认知发展的教师心理大体一致。
hellip;hellip;
五、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和涂尔干的'集体意识':作为无意识社会学的想象吸收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捕捉到了一个原型想象的共性,即他后来在炼金术中的工作显示出植根于抽象的物理隐喻。它们必须具有跨文化的元素,但它们所阐述的神话只有在明确地作为文化传承的地方才会是“祖先”或“种族”。荣格试图将这种共性——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捕捉为生物学家进化或系统发育的无意识,但错过了他的集体无意识在语用上与涂尔干(1912)纯粹社会学意义上的“集体意识”概念完全相同,特别是在以神话为中心的民族中发现的。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这样一种集体共享的调适,被全社会的梦想共享所强化,并向持续的'有意义的巧合'敞开,像外化的主动想象。这种被阐释的集体意识随着我们对这些隐喻性的外化失去了接触而变得无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隐含在我们身上。群体乐观悲观的民意调查和对大众传媒的研究,反映在当代社会学中,我们的集体意识因此变得不再那么普遍,而是更加稚嫩和模糊。
荣格显然没有阅读《文集》中无处引用的涂尔干本人。但他的确把涂尔干的萨社人休伯特和毛斯关于神话和仪式的lsquo;集体表征rsquo;解释为他的lsquo;继承原型rsquo;的独立平行。荣格显然怀念他们的lsquo;先验范畴rsquo;纯粹是涂尔干lsquo;集体意识rsquo;的社会文化版本。相应地,涂尔干错过的是,在共同的物理隐喻和通感联想中的“集体表象”基础(正如最近在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认知心理学中发展的那样),为他的社会集体意识增加了跨文化成分,从而使他惊人地接近荣格。
对于荣格来说,“集体表象”中的跨文化共性只能从生物学上解释。这在他看来很可能是公理化的,因为他非常需要科学上的“坚实”和“深刻”支持他自己强大的、常常令人不安的经历,正如红书(2009年)中所充分记载的那样。然而,他自己对无政府主义心理学的解释,是建立在回归自然的基础上的,不可知论和文艺复兴炼金术是隐喻西方丰富精神系统的最后一个位置。简言之,它们是社会文化和历史文化。沙姆达萨尼在《红书》(2009)的注释中引用荣格的话说,“回到中世纪的运动hellip;hellip;是历史的回归,是对集体无意识过去的回归”。这几乎不是对任何生物的、种族的、或植物学的回归,而是对作为lsquo;心理学rsquo;的它的更新和重述的断裂文化脉络的拾取。
在现代西方,由于我们的极端个人主义,不可避免地被荣格自己所认同,我们往往会错过表面上高度想象力吸收和光彩照人的个别国家的社会集体性质。的确,现代创作者可以特别感到孤独和孤立,正如荣格本人在《红书》中对疯狂的恐惧。然而,当代大众社会采用创造性突破的速度也意味着,越是深入'下行'和'内在'通感中介的'意识状态的改变'和'原型意象',就越是同时'外出'如果是隐性的,则进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沿着这些脉络,后来的荣格(1955)指出:lsquo;个人原型想象使意识到什么补偿了集体的社会苦难rsquo;(p 550)。对想象性意识状态的深度吸收也是对社会领域的深度吸收,而不是对普通意识的深度吸收,因为这类人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所有思想的隐喻和通感层面,不管这是否被现存神话的外化隐喻所呈现。
六、荣格的《红书》、《涂尔干与未来的宗教: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学想象》
荣格的《红书》作为其后期较为正式的创作的远见来源,与涂尔干本人基于激进的个人个性化对现代'集体意识'发展为'未来的宗教'的推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1898年发表的《个人主义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迪尔凯姆谈到了他所处时代日益世俗化的问题,并预见未来的精神性将逐渐从个人价值的日益提高以及现代西方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中演变出来。他称之为'人的崇拜',建立在自由个体共同的集体基础之上,每个个体都发展到最大的个人潜能。泰西非常有自己诺斯替主义的和尼采式的泛音:
除了人本身,没有什么是男人所爱和尊敬的。这就是为什么人成了人的神,为什么他不能再转向别的神而不再对自己不真实。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体现着某种人性的东西一样,每个个体都有某种神圣的东西,使之神圣不可侵犯的牙人。(迪尔凯姆1898,P.26)
对于涂尔干来说,宗教是任何在最深层次上将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这里要以个人为基础。因此,这就是宗教,尽管它最大限度地消减了人的注意力,并最终基于人本身的品质。涂尔干本人并没有对个体存在的这一本质做进一步的探讨,但随后20世纪这一主题的发展包括海德格尔(1927)的达辛现象学、马斯洛(1962)和阿尔马斯(1996)关于自我实现的跨个人心理学,作为我们个人存在最终精神实现的潜能,人在无知状态下的身份成为存在本身,当然也成为自我。
《红书》除了从1913年末开始对荣格的经历进行个人的文献整理外,同样也是自己对未来的一种后尼采宗教的尝试。荣格只是在1915年才开始把他早些时候的笔记本转化为《红书》的书画,此后他终于相信,他对世界毁灭的积极想象和梦想并没有预示着一种恐惧和失控的精神分裂症。相反,他来把它们看作是对社会——历史集体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 collective unconscious reconsidered: Jungrsquo;s archetypal imagination in the light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Harry T. Hunt, Ontario, Canada
Abstract: A needed rapprochement between Jung and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may rest less on the much debated relevance of a biologistic collective unconscious than on a re-inscribing of an archetypal imagination,as the phenomeno-logical and empirical core of Jungian psychology.The most promising approaches in this regard in term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psychology come from combining 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metaphor and synaesthesia,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aginative absorption and openness to numinous experience and spirituality as a form of symbolic intelligence.On the socio-cultural side,this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archetypal imagination is also congruent with Leacute;vi-Strauss on the metaphoric roots of mythological thinking,and Durkheim on a sociology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This conjoined perspective,while validating the cross cultural commonality of physical metaphor intuited by Jung and Hillman on alchemy,also shows Jungrsquo;s Red Book,considered as the expressive source for his more formal psychology,to be far closer in spirit to a socio-cultural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based on metaphoric imagination,than to a phylogenetic or evolutionary unconscious.A mutual re-inscribing ofJung into congruent areas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anthropology,sociology,and vice versa,can help to further validate Jungrsquo;s key observations and is fully consistent with Jungrsquo;s own early efforts at synthesis within the human sciences.
Key word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maginative absorption, Leacute;vi-Strauss, metaphor, numinous experience, personal intelligence, synaesthesia, unus mundus
Introduction
As someone who entered academic psychology on the basis of my readings in Jung,which have continued to inform my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writings(Hunt 1989,1995a,2003),I can only regard the increasing exclusion of Jungian psychology from psychology textbooks and courses in personality as deeply unfortunate.Meanwhile,the frequent dismissal by clinically trained Jungians of congruent academic research in psych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as irrelevant to the unique individuality of therapist-patient dialogue is correspondingly short-sighted,especially given Shamdasanirsquo;s(2003)detailed demonstration of Jungrsquo;s own efforts to integrate the archetypal experiences of a collective unconscious with the psychology,anthropology,and sociology of his day.
In what follows I will b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Jungrsquo;s descriptive concentration on the phenomena of myth, religion, and the archetypal imagery of numinous experience as applied to individual child and adult development which I consider to be the empirical core of his psychology. There is a largely unremarked congruence between this core and more recent research in areas as diverse as:
bull;the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metaphor;
bull;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maginative absorption as predictive of openness to vivid dreaming, creativity, and transpersonal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bull;spirituality as a higher form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ull;the anthropology of shamanism and mythological thinking;
bull;the sociology of consciousness as itself already inherently collective.
A major focus of this paper will be on some key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within Jungrsquo;s concept of a collective unconscious that can render it progressively out of tune with these otherwise supporting developments in academic psych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corresponding ways of re-inscribing Jungian psychology, already implicit in Jungrsquo;s own writings, that show its deeper resonance with these developments.
Less central here will be both the recent attempts to show the consis-tency of Jungrsquo;s collective unconscious with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and the many post-modern hermeneutic re-readings of Jung.With respect to the former,while it is certainly of interest that Jungrsquo;s later formulation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can be shown to be variously consistent with the neuroscience of innate behaviours(Goodwyn 2010;Stevens 2003),the Baldwin effect(Hogenson 2001),and self-organizing system approaches(Merchant 2009),it is not clear how evolutionary theory,whether Jungrsquo;s own or recent formulations,actually has any direct logical or deductive connection to what Hillman(1975)and Corbett(1996)see as the empirical core of Jungrsquo;s psychology in the experiential phenomena of archetypal imagination and numinous experience.Indeed,these phenomena,which are highly congruent with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metaphor and imagination(Hunt 1995a),seem to be equally consistent with some very different macro models of evolution.Meanwhile purely hermeneutic approaches to Jung,while undoubtedly liberating in clinical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s(Hauke 2000),too often entail an attendant dismissal of any relevance to thelsquo;positivisticrsquo;human sciences.This only increases their isolation from academic circles and is inconsistent with Jungrsquo;s own hopes for continue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original founding of the Zurich training institute(Meier 2001).
Contradictions in Jungrsquo;s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nd their potential resolution in the cognitive-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of metaphor
Both Jungrsquo;s earlier(1912)and later(1954)formulations of a collective unconscious that would account for cross-cultural commonalities in mythology and the forms of numinous experience at the core of the world religions contain an implicit conflict and conceptual tension.
On the one hand,archetypal imagination is the source of imagistic creativity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Jung(1912)makes clear that it is not in itself infantile or childlike,but rather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5269],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