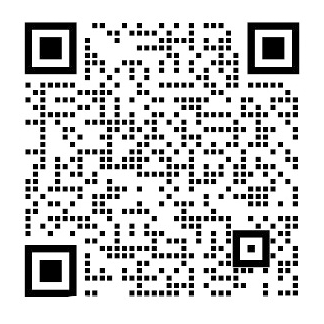承认文化维度在数学教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原文作者 Paul Andrews
单位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摘要:本文共分四个部分,作者恳请从事教学研究的人认识到,教学的工作是在一种文化中进行的。第一部分考察了文化的三种主要模式及其对教育的意义,第二部分通过对各种课程模式的批判,进一步强调文化对儿童期望的影响。第三部分考察了文化在欧洲数学课程的特殊性,而第四部分则探讨了数学教学中的文化差异。从而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比现在更明确地承认,文化需要渗透到教育的各个方面。
关键词:比较数学教学;文化;数学教育研究
文化与数学课程
上述所讨论的基本原则和传统在学校数学的书面表达或预期表达中体现的程度可能因国而异。此外,为了便于讨论,Mason (2007, P172)指出课程是“物质的人工产物”,是文化人类学家的领域,也是“符号系统”,是文化社会学家的领域。也就是说,课程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包括“群体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以及在群体内部构建和共享意义的实践(Mason, 2007: 172)。在详细阐明他们与霍夫斯塔德文化纬度之间的关系之前,以下明示了四种欧洲观点(背景)下的初等高中线性方程的教学(方法)。这样,作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实体的课程如何建构就变得很清楚了。关于受审查国家的选择受到英文课程供应的限制,而主题则由我目前从事的其他工作决定。它们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在线性方程方面,在基于web的文档允许的范围内是逐字逐句的。
英国国家课程规定,11-14岁的学生“应该能够hellip;hellip;处理数字、代数表达式和方程,并应用常规算法”。它接着说,“数学学习应该包括hellip;hellip;”“线性方程、公式、表达式和恒等式”和“解析、图解和数值解方程方法”。这是伴随着一个解释性的说明,说线性方程“包括建立方程,包括不等式和联立方程。学生应该能够识别无解或无穷多解的方程”。目前文件中所有剩下的对等式的引用都暗指对学生学习的评估,以及在欧洲体系中,英国对学生成绩应用等级的独特传统。
芬兰国家6-9年级的课程规定,学生到8年级结束时,“将知道如何hellip;hellip;解出一级方程式”。
佛兰德的数学课程要求中学一年级的学生“用一个未知的简单问题解出一年级的方程,并将其转化为这样的方程”。在二年级期间,他们将“解决一个未知数的一阶和二阶方程,以及可以转换成这种方程的问题”。
匈牙利5-8年级(小学高年级)的课程规定,五年级的学生应该“通过演绎、分解、替换和口头表达的简单问题来解决第一级的简单方程”。 6年级“用自由选择的方法解一阶一元方程”。到第7年,他们应该“通过演绎和平衡原理来解一阶简单方程”。翻译文本并解决口头表达的问题。用图解法求解一阶一元方程组。最后,到八年级时,学生应“解出一阶与基集和解集有关的演绎方程,分析文本并将其翻译成数学语言,解决口头表达的数学问题。”
在这四个例子中,不仅可以看到对初中课程这个核心话题的不同的观点。英文和芬兰文的文件都对这个主题的性质以及应如何涵盖这个主题提出了松散、与时间无关的观点。例如,英国的文件涵盖了3年的教育,芬兰的文件涵盖了4年,但都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时候应该涵盖材料。这两份文件都没有指定任何特定的方法或方法,尽管英国人期望,在一般的程序预期中,学生应该接触解析法、图解法和数值法。两份文件都没有明确提到关于方程的问题解决或文字问题以及从文本推导方程。佛兰德斯的文件似乎更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就线性方程而言,从一年到下一年的变化似乎含糊不清。主要的区别在于明确地期望问题能转化为方程来求解。最后,匈牙利语的课程在四年的时间里提供了严格规定的进展,方法和问题的解决,包括文字问题,越来越多的利用。
那么,这些文化规范和社会行为的特征模式是如何在数学课程介绍中找到自己的声音的呢?在我看来,对课程期望最宽松的两个国家,英国和芬兰,反映了权力距离、横向文化(Triandis, 2001)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的文化。换句话说,低权力距离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在这种文化中,课程开发人员期望并相信负责课程交付的人会适当地这样做。事实上,霍夫斯泰德(1980年,第46页)在谈到低权力距离文化时写道,“处于不同权力级别的人感觉hellip;hellip;准备信任他人”。就低不确定性规避而言,松散结构课程反映了社会规范,其中不仅是“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是更容易接受和每一天都当作是“还容忍异议和偏差的文化,人们愿意冒险(霍夫斯泰德,1980年,P47)。比利时的情况则不同。相对高水平的权力回避和不确定性回避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佛兰德斯当局制定了比英语或芬兰人更严格的课程结构。此外,人们可能会猜测,严格规定的匈牙利课程将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文化中,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高于其他三个受到审查的国家。
简而言之,虽然最后一段有点推测性,但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是,数学课程的不同表现是文化本身的基本结构的显著差异的结果。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考虑了这种差异是如何在数学课堂中发挥作用的。
文化与数学教学
如上所述,教师是教育系统价值的代理人,根据上面所讨论的各种文化和课程模式,如果,教师的行为不能反映这些模式,那将是令人惊讶的。的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们必然而且可能不知不觉地以反映这些目标和价值的方式运作。他们会对特定的成果给予特权,他们会利用特定的教学策略,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老师区分开来。例如,Hess和Azuma(1991),在日本和美国学校的组织结构和程序对学习造成了障碍,这两个国家的教师以不同的、但受文化影响的方式来调解这些障碍。日本教师倾向于采取注重学习者促进性倾向发展的策略,而美国教师倾向于使学习过程更具吸引力。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教师的行为方式与东方教师不同。在这方面,许多研究人员强调了苏格拉底哲学和儒家哲学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的影响(Leung, 2001; Tweed amp; Lehman, 2002; Watkins, 2000)。的确,在数学方面,梁(2001)提出了六个东亚和西方数学课堂之间的二分法,位于儒家与苏格拉底的辩论:(a)产品(内容)与过程,(b)机械学习与有意义的学习,(c)努力学习和愉快的学习,(d)外在与内在动机,(e)全班教学和个性化学习,(f)教师能力与标的物与教育学的争论。然而,这样的区分不可避免地是粗糙的,有时可能是不准确的。例如,Mason(2007)认为这种区分不仅笨拙,而且经常滑入无意识的刻板印象甚至种族主义。
结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证明教与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活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课程,尤其是数学课,“经常有一种惯例,以确保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它们是“教学和学习的日常程序,通常以一种被每种文化普遍接受的某种方式组织起来”(Kawanaka, 1999, p.91)。这种可预测的规律被各种各样地描述为课堂数学的传统(科布等人)。《文化脚本》(Stigler and Hiebert, 1999),《课程签名》(Hiebert等人)。或一节课的典型教学流程(Schmidt等人)。(Cogan amp; Schmidt, 1996),后者体现了通过反复制定的教学策略,这些策略是典型的国家教育策略,也是大多数教师意识不到的(Cogan amp; Schmidt, 1999)。通过这种方式,文化“塑造了国家内部的课堂过程和教学实践,以及学生、家长和教师如何看待它们”(Knipping, 2003, p.282)。事实上,这种文化的潜在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致许多教学过程都“深深植根于学校教育过程的背景之中hellip;hellip;所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hellip;hellip;是不值一提的”(Huftonamp; Elliott, 2000, p.117)。
外文文献出处:Acta Didactica Napocensia,2010
附外文文献原文
The importance of acknowledging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Culture and mathematics curricula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and traditions discussed above find manifestation in the written, or intended, presentation of school mathematics may vary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Moreover, by way of facilitating discussion, Mason (2007, p. 172) notes that a curriculum is “both material artefact”, the domain of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and “symbolic system”, the domain of the cultural sociologist. That is, the curriculum reflects both a way of life, including the “shared values and meanings common to members of the group” and the practices by which meaning is constructed and shared within the group (Mason, 2007: 172). In the following four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he teaching of linear equations at the lower secondary level are presented before being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Hofstedes dimensions of culture. In so doing, it is becomes clear how curricula, as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entities, are constructed. Choice, in respect of the countries under scrutiny, was constrain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curricula in English, while the topic was determined by other work on which I am currently engaged. They are presented alphabetically and, in respect of linear equations, verbatim as far as web-based documents allow.
The English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students in the age range 11-14 asserts that pupils “should be able to... manipulate numbers, algebraic expressions and equations and apply routine algorithms”. It then goes on to say that the “study of mathematics should include... linear equations, formulae, expressions and identities” and “analytical, graphical and numerical methods for solving equations”. This is accompanied by an explanatory note, saying that linear equations “includes setting up equations, including inequalities and simultaneous equations. Pupils should be able to recognise equations with no solutions or an infinite number of solutions”. All remaining references to equations in the current document allude to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rsquo; learning and the unique, among European systems, English tradition of applying levels to studentsrsquo; achievement.
The Finnish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grades 6-9 asserts that students, by the end of grade 8, “will know how tohellip; solve a first degr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承认文化维度在数学教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原文作者 Paul Andrews
单位 Faculty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摘要:本文共分四个部分,作者恳请从事教学研究的人认识到,教学的工作是在一种文化中进行的。第一部分考察了文化的三种主要模式及其对教育的意义,第二部分通过对各种课程模式的批判,进一步强调文化对儿童期望的影响。第三部分考察了文化在欧洲数学课程的特殊性,而第四部分则探讨了数学教学中的文化差异。从而得出结论:我们应该比现在更明确地承认,文化需要渗透到教育的各个方面。
关键词:比较数学教学;文化;数学教育研究
文化与数学课程
上述所讨论的基本原则和传统在学校数学的书面表达或预期表达中体现的程度可能因国而异。此外,为了便于讨论,Mason (2007, P172)指出课程是“物质的人工产物”,是文化人类学家的领域,也是“符号系统”,是文化社会学家的领域。也就是说,课程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包括“群体成员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以及在群体内部构建和共享意义的实践(Mason, 2007: 172)。在详细阐明他们与霍夫斯塔德文化纬度之间的关系之前,以下明示了四种欧洲观点(背景)下的初等高中线性方程的教学(方法)。这样,作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实体的课程如何建构就变得很清楚了。关于受审查国家的选择受到英文课程供应的限制,而主题则由我目前从事的其他工作决定。它们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在线性方程方面,在基于web的文档允许的范围内是逐字逐句的。
英国国家课程规定,11-14岁的学生“应该能够hellip;hellip;处理数字、代数表达式和方程,并应用常规算法”。它接着说,“数学学习应该包括hellip;hellip;”“线性方程、公式、表达式和恒等式”和“解析、图解和数值解方程方法”。这是伴随着一个解释性的说明,说线性方程“包括建立方程,包括不等式和联立方程。学生应该能够识别无解或无穷多解的方程”。目前文件中所有剩下的对等式的引用都暗指对学生学习的评估,以及在欧洲体系中,英国对学生成绩应用等级的独特传统。
芬兰国家6-9年级的课程规定,学生到8年级结束时,“将知道如何hellip;hellip;解出一级方程式”。
佛兰德的数学课程要求中学一年级的学生“用一个未知的简单问题解出一年级的方程,并将其转化为这样的方程”。在二年级期间,他们将“解决一个未知数的一阶和二阶方程,以及可以转换成这种方程的问题”。
匈牙利5-8年级(小学高年级)的课程规定,五年级的学生应该“通过演绎、分解、替换和口头表达的简单问题来解决第一级的简单方程”。 6年级“用自由选择的方法解一阶一元方程”。到第7年,他们应该“通过演绎和平衡原理来解一阶简单方程”。翻译文本并解决口头表达的问题。用图解法求解一阶一元方程组。最后,到八年级时,学生应“解出一阶与基集和解集有关的演绎方程,分析文本并将其翻译成数学语言,解决口头表达的数学问题。”
在这四个例子中,不仅可以看到对初中课程这个核心话题的不同的观点。英文和芬兰文的文件都对这个主题的性质以及应如何涵盖这个主题提出了松散、与时间无关的观点。例如,英国的文件涵盖了3年的教育,芬兰的文件涵盖了4年,但都没有具体规定什么时候应该涵盖材料。这两份文件都没有指定任何特定的方法或方法,尽管英国人期望,在一般的程序预期中,学生应该接触解析法、图解法和数值法。两份文件都没有明确提到关于方程的问题解决或文字问题以及从文本推导方程。佛兰德斯的文件似乎更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就线性方程而言,从一年到下一年的变化似乎含糊不清。主要的区别在于明确地期望问题能转化为方程来求解。最后,匈牙利语的课程在四年的时间里提供了严格规定的进展,方法和问题的解决,包括文字问题,越来越多的利用。
那么,这些文化规范和社会行为的特征模式是如何在数学课程介绍中找到自己的声音的呢?在我看来,对课程期望最宽松的两个国家,英国和芬兰,反映了权力距离、横向文化(Triandis, 2001)和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的文化。换句话说,低权力距离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在这种文化中,课程开发人员期望并相信负责课程交付的人会适当地这样做。事实上,霍夫斯泰德(1980年,第46页)在谈到低权力距离文化时写道,“处于不同权力级别的人感觉hellip;hellip;准备信任他人”。就低不确定性规避而言,松散结构课程反映了社会规范,其中不仅是“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是更容易接受和每一天都当作是“还容忍异议和偏差的文化,人们愿意冒险(霍夫斯泰德,1980年,P47)。比利时的情况则不同。相对高水平的权力回避和不确定性回避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佛兰德斯当局制定了比英语或芬兰人更严格的课程结构。此外,人们可能会猜测,严格规定的匈牙利课程将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文化中,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高于其他三个受到审查的国家。
简而言之,虽然最后一段有点推测性,但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是,数学课程的不同表现是文化本身的基本结构的显著差异的结果。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考虑了这种差异是如何在数学课堂中发挥作用的。
文化与数学教学
如上所述,教师是教育系统价值的代理人,根据上面所讨论的各种文化和课程模式,如果,教师的行为不能反映这些模式,那将是令人惊讶的。的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们必然而且可能不知不觉地以反映这些目标和价值的方式运作。他们会对特定的成果给予特权,他们会利用特定的教学策略,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老师区分开来。例如,Hess和Azuma(1991),在日本和美国学校的组织结构和程序对学习造成了障碍,这两个国家的教师以不同的、但受文化影响的方式来调解这些障碍。日本教师倾向于采取注重学习者促进性倾向发展的策略,而美国教师倾向于使学习过程更具吸引力。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教师的行为方式与东方教师不同。在这方面,许多研究人员强调了苏格拉底哲学和儒家哲学对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的影响(Leung, 2001; Tweed amp; Lehman, 2002; Watkins, 2000)。的确,在数学方面,梁(2001)提出了六个东亚和西方数学课堂之间的二分法,位于儒家与苏格拉底的辩论:(a)产品(内容)与过程,(b)机械学习与有意义的学习,(c)努力学习和愉快的学习,(d)外在与内在动机,(e)全班教学和个性化学习,(f)教师能力与标的物与教育学的争论。然而,这样的区分不可避免地是粗糙的,有时可能是不准确的。例如,Mason(2007)认为这种区分不仅笨拙,而且经常滑入无意识的刻板印象甚至种族主义。
结论
在这篇论文中,我试图证明教与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活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课程,尤其是数学课,“经常有一种惯例,以确保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它们是“教学和学习的日常程序,通常以一种被每种文化普遍接受的某种方式组织起来”(Kawanaka, 1999, p.91)。这种可预测的规律被各种各样地描述为课堂数学的传统(科布等人)。《文化脚本》(Stigler and Hiebert, 1999),《课程签名》(Hiebert等人)。或一节课的典型教学流程(Schmidt等人)。(Cogan amp; Schmidt, 1996),后者体现了通过反复制定的教学策略,这些策略是典型的国家教育策略,也是大多数教师意识不到的(Cogan amp; Schmidt, 1999)。通过这种方式,文化“塑造了国家内部的课堂过程和教学实践,以及学生、家长和教师如何看待它们”(Knipping, 2003, p.282)。事实上,这种文化的潜在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致许多教学过程都“深深植根于学校教育过程的背景之中hellip;hellip;所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hellip;hellip;是不值一提的”(Huftonamp; Elliott, 2000, p.117)。
外文文献出处:Acta Didactica Napocensia,2010
附外文文献原文
The importance of acknowledging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Culture and mathematics curricula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and traditions discussed above find manifestation in the written, or intended, presentation of school mathematics may vary from one country to another. Moreover, by way of facilitating discussion, Mason (2007, p. 172) notes that a curriculum is “both material artefact”, the domain of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and “symbolic system”, the domain of the cultural sociologist. That is, the curriculum reflects both a way of life, including the “shared values and meanings common to members of the group” and the practices by which meaning is constructed and shared within the group (Mason, 2007: 172). In the following four European perspectives on the teaching of linear equations at the lower secondary level are presented before being discussed in relation to Hofstedes dimensions of culture. In so doing, it is becomes clear how curricula, as anthrop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entities, are constructed. Choice, in respect of the countries under scrutiny, was constrain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curricula in English, while the topic was determined by other work on which I am currently engaged. They are presented alphabetically and, in respect of linear equations, verbatim as far as web-based documents allow.
The English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students in the age range 11-14 asserts that pupils “should be able to... manipulate numbers, algebraic expressions and equations and apply routine algorithms”. It then goes on to say that the “study of mathematics should include... linear equations, formulae, expressions and identities” and “analytical, graphical and numerical methods for solving equations”. This is accompanied by an explanatory note, saying that linear equations “includes setting up equations, including inequalities and simultaneous equations. Pupils should be able to recognise equations with no solutions or an infinite number of solutions”. All remaining references to equations in the current document allude to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rsquo; learning and the unique, among European systems, English tradition of applying levels to studentsrsquo; achievement.
The Finnish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grades 6-9 asserts that students, by the end of grade 8, “will know how tohellip; solve a first degr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2028],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