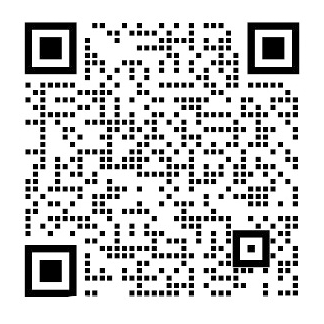美国公立学校体罚的使用现状
美国公立学校对学生体罚的使用非常普遍据介绍,一份学校纪律调查表已邮寄给18个国家的324名校长随机选择代表美国九个人口普查区的州。结果表明,体罚在每个年级的学生中都广泛使用几乎在美国所有地区都达到这一水平。使用的说明提供并讨论了涉及人口统计、行政程序和行政意见变量的体罚。本文还讨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和教学启示。
学校工作人员使用体罚作为一种纪律手段已经持续多年在不同的时期,体罚要么被提倡,要么被谴责,并且它是关于伦理、道德、合法性和效力问题的众多争议的起因,最近发生的两起事件使体罚重新成为教育争议的中心。首先,美国最高法院在Ingraham v。赖特(1977)指出,体罚并不违反宪法对残忍和不寻常惩罚的保障。第二,最近呼吁在教育和纪律实践中“回归基础”,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学校体罚的认可(例如,威尔士,1978年)。支持者建议体罚,惩罚可以快速减少或消除行为,促进惩罚学习,并替代阻止同龄人的类似不当行为体罚也可能受到青睐,因为它快速、容易获得,而且明显有效。反对使用体罚的许多论点已经提出,包括:(a)个人尽可能退出惩罚情境的可能性 (b) 模拟实施惩罚的行为(班杜拉,1965年)(c) 提请注意受惩罚的行为,在老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其他学生可能会发出这种行为(Bandura,1965);对接受惩罚的儿童产生负面的同伴反应缺乏对不同环境的概括效应(f)引起攻击性反应,包括操作性攻击(即攻击惩罚来源);Delgado,1963),并引发攻击(即针对环境中其他人或财产的攻击;无论人们对体罚持何种立场,越来越明显的是,大多数专业和公众舆论更多地是由直觉、民间传说和猜测而非经验证据形成的。似乎没有基于经验的应用研究支持体罚的使用。相反,支持性证据似乎来自临床实践或轶事现场研究。已发表的评论表明,在适用的环境中,惩罚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知的;尽管缺乏研究支持,体罚仍然在公立学校使用。我们不仅对体罚的效果知之甚少,而且同样缺乏关于体罚在公立学校使用的描述性信息。本研究的目的是描述美国公立学校学生使用体罚的报道。
方法。
选举答卷人
最初,从美国九个人口普查区中随机抽取两个州。使用Patterson的《美国教育》(1980),从18个选定的州中随机选择了10个学区。向180个选定学区的每一位校长发送了一封信,要求列出他们所在学区的校长名单,并解释提出要求的原因(即缺乏有关纪律实践的经验信息,同时要求回归基础,以及这些因素对未来实践的影响)。在选定的答复截止日期后2周内未作出答复的主管收到了后续信函或电话。从103名主管(57%)处获得可用信息。那些拒绝参与、地区规定禁止参与或提供不完整信息的人被归类为不可用的响应。最后,从每个可用学区选择校长,以接收学校纪律调查表。各州选择的学校数量略有不同,这取决于地区主管的可用回复数量。因此,在18个预选州中选择了324所学校。对学校进行年级控制,并通过随机选择过程控制所有其他人口统计学变量(如社区规模、学生人数和校长性别)。特殊学校(如特殊教育中心或职业/技术学校)被排除在外。每所学校的校长都收到了一封信,解释了研究的基本原理、他们参与的自愿性质、小组数据的使用,以及与学校纪律调查表一起分享结果的提议。不进行了随访,主要是因为学年快结束了。232名校长(71%)返回了可用信息。那些拒绝接受顶级推荐或提供不完整信息的人被归类为无法使用的回复。
受访者。
由于未获得任何个人信息,因此对受访者了解甚少。调查对象的性别是根据他们公开的姓名推断出来的。然而,在一些情况下,校长使用的是首字母缩写而不是名字,或者名字没有表明性别(例如Pat)。当性别是一个变量时,这些校长的回答被排除在数据分析之外。表1给出了受访者数量的描述。
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询问了这些赞助者的人口统计以及他们对体罚的使用情况。它的目的是尽可能少的努力获得最多的描述性信息。在与本报告密切相关的22个问题中,除1个问题外,所有问题都通过从中选择答案来回答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选择或要求回答“是”或“否”。其余项目要求提供无法预测的信息(即,哪些行为受到惩罚)。
结果。
如果将从学校纪律调查中获得的数据分为四类,则最容易对其进行分析:(a)一般结果,(b)人口统计结果,(c)行政/程序和(d)行政意见。
一般结果
关于使用体罚的一般性质的数据如下:编译。表2给出了对该表中每个项目的响应频率分布问卷调查如表2所示,74.1%的校长表示他们对学生进行体罚。
人口统计结果
人口统计结果包括通过个人、地理或学校相关变量分析时对体罚不同使用的描述。下面讨论这些人口统计结果。校长的性别。当使用卡方检验法分析校长性别与体罚使用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存在显著差异:x2(1raquo;n=228)=5.24,p=0.02。如表3所示,100%的女校长报告使用体罚,而70.3%的男校长报告使用体罚。显然,校长的性别与体罚的使用之间存在关系:女性比男性同事更可能使用体罚。此外,仅男性校长报告的体罚频率较高:没有女性校长报告每月有15名学生以上使用体罚,而17.4%的男性校长报告每月有20名学生以上使用体罚(值得注意的是,88.6%的受访者为男性。1)按社区规模、地区或年级水平分析时,没有发现校长性别的差异影响。
社区规模。
当使用社区规模作为自变量分析体罚的使用时,发现显著差异:x2(7gt;N=232)=18.38,p=0.01。被调查者学校所在社区的规模与体罚的使用之间似乎呈反比关系。因此,较小社区的学校校长报告说使用体罚的比例过高,而较大社区的学校校长报告使用体罚的比例相对较低。读者可参考表4,了解对该项目的响应的定量描述。按区域分析时,没有发现社区规模的差异效应。
学校体罚禁令:教师态度与课堂实践
小学教育专业 齐浩 指导老师:陈琦
摘要:本研究考察了印度教师对体罚(CP)的看法、尽管有禁令,但体罚仍然存在的原因,以及体罚争议反映学校社会氛围的方式。本定性研究借鉴了有关学生控制和系统理论的监护观点的文献,主要通过观察和访谈来检验印度德里教师对使用CP的看法。根据数据分析,本研究得出结论,CP的替代方案和CP禁令的成功实施取决于地方和国家社会文化规范之间的兼容性、教师对政策目标的态度和信念以及资源的可用性。这项研究有助于理解教育家对体罚的理解,认为体罚是一种纪律工具,可以促进社会中有意义的行动和变革。此外,本研究为决策者制定公平的政策创造了环境,这些政策能够帮助教师有效地处理学生的不当行为,并创造安全的学习环境。
关键词:印度;教育改革;课堂实践;体罚
作为社会成员,学生越来越被视为有权在没有强迫的环境中接受教育(Durrant和Smith,2011;帕特和古尔德,2012年)。199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Tiwari 2014,2015a)就是这种向无胁迫教育环境概念转变的范例,其中183个国家签署了该公约禁止对儿童体罚的决议。在签署国中,一些国家目前正在制定法律,另一些国家已制定法律,而一些国家尚未采取行动禁止CP。根据《结束体罚》(2012年)编制的清单,有33个国家禁止针对儿童的各种CP,这种做法继续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学生中广泛使用。在禁止这种做法最成功的国家中,大多数是使用严格法律和宣传运动的非英语国家。其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将CP纳入重大的法律改革和改革
社会政策。
然而,就学校而言,禁止CP的协议并非在所有国家都有相同的规范性支持基础。例如,尽管西方国家的学生越来越反对学校CP,但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学生可能倾向于从成年人那里获得CP。例如,拯救儿童组织(Save the Children,2005年)进行的一项蒙古调查发现,年龄在10-14岁之间的学生中,78%认为他们对CP负责,成年人有权实施CP。英国在1987年禁止了学校CP;但一些研究表明,围绕这一学科的信仰体系没有改变。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近一半的英国家长在学校里支持CP,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有效控制学生和提高学习成绩的手段。这可能部分源于英国学校欺负学生、逃学和课堂秩序混乱案件的增加,这反过来引发了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对学校安全和礼仪需要的讨论。
事实上,CP在英国及其前殖民地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做法在前英联邦的地位让人想起它在殖民时代的使用;例如,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政治压迫的一种手段(Raj 2011)。其中一些国家在禁止CP方面进展缓慢。例如,在澳大利亚,CP在学校和家庭中都是合法的。2011年,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地区的公民拒绝了禁止在家中使用CP的立法提案(2012年结束体罚)。尽管澳大利亚政府表示,他们致力于促进学生的安全学校,但根据法律,CP仍然是允许的。
CP的持续存在可能是由于司法系统执法不力(Durrant和Smith,2011年)或对立法语言的松散解释造成的。例如,阿根廷法律禁止在学校进行这种做法,强调了保护儿童身体完整的重要性。然而,法律对CP的模糊定义允许教师在学校继续使用“轻微”打屁股作为行为矫正和学生控制的手段(Romero 2002)。
与教师有关的因素,如教育准备和资源,导致许多中东国家的学校继续使用体罚。Benbenishty等人(2002年)在对以色列小学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压力大、资源少的学校,学生受到虐待的现象普遍存在。他们发现,由于缺乏其他纪律手段,教师更有可能诉诸攻击(Benbenishty等人,2002;霍里·卡萨布里(2006年)。阿拉伯文化是由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塑造的性格,它支持用惩罚来惩罚学生。美国尚未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禁止学校CP的决议。这种情况是最高法院在1977年Ingraham v.案中裁决的结果之一。Wright,该公司认为,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政策禁止其使用的情况下,CP既不是非法或侵犯学生的宪法权利(Gershoff 2002;结束体罚(2012年)。因此,法院的判决允许各州和学区继续采用不同的立法和行政活动标准和模式(Hyman,1990年)。
Gershoff(2002)的一项元分析审查报告称,美国对“可接受的体罚和危险的身体虐待”之间的界限缺乏共识(540)。尽管50个州中有31个州宣布CP为非法,许多地方学区也取消了CP,但随着所谓“无借口”特许学校的发展,这种严厉的惩罚又卷土重来,即使不属于CP的模糊定义,也可能对心理造成伤害。例如,最近爆发了争议,在一段被泄露的视频中,一名一年级教师因一名孩子在纽约市成功学院数学错误而斥责他,这反过来又引起了专家们的强烈谴责。
根据《结束体罚》(2012年),CP仍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原则、政策和CP使用之间的脱节似乎反映了教师-家长对学生控制和宗教文化历史影响的关注(Lwo和Yuan,2010;韩寒2011;帕特和古尔德,2012年)。然而,关于在学校中实施CP的合法性的辩论提出了关于CP的全球地位及其文化影响的问题。
印度背景下的体罚
CP是印度学校严格纪律和学生控制的常用方法之一。一些教师认为,任何违规行为的直接后果都会维持一个有序的环境,而CP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合适工具,尤其是在过于拥挤的教室里。教师通常将CP视为一种快速有效的惩罚方法,并对未来的干扰起到威慑作用,尤其是在公开向其他学生发出警告信息时(蒋,2009)。因为学校校长很少干预课堂纪律问题(Wallace、Sung和Williams,2014),教师被暗中鼓励——并且更有可能——制定自己的纪律守则,而不是求助于全校的行为守则(Anderson和Payne 1994;Cheruvalath和Tripathi,2015年)。此外,印度公立学校教师在社区中发挥着多种作用。他们不仅教授教室,还协助地方政府进行人口普查、选举、根除脊髓灰质炎和午餐计划(Tiwari 2014)。因此,这些教师被视为当地导师和道德领袖,能够教导学生错误行为。尽管印度教师被允许使用CP来纠正不良行为或学业成绩,但他们开始受到最近全球对这种做法的蔑视的转变的影响(Tiwari 2014,2015a,2015b)。过去十年来,印度学校对使用CP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关键政策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例如,2000年,德里高等法院发布了一项裁决,规定学校应将CP定为非法,每个学区应实施终止这种做法的指导方针(Bhowmick 2009)。一些学校成立了特别工作组来评估这种做法,一些地区向当地学校发出备忘录,敦促他们停止这种做法。2010年,印度立法机构的《受教育权法》(RTE)宣布私立和公立学校的CP为非法。立法要求学校避免体罚,精神骚扰,
以及对学生的歧视。尽管如此,此类司法和立法行动对于消除学校中使用CP或改变公众对什么是合法纪律的看法(Bhowmick2009;2011年全国保护儿童权利委员会;蒂瓦里(2014年)。报纸和非政府组织继续定期报道CP病例。2011年,国家儿童权利保护委员会(NCPCR)进行的一项七州调查发现,99%的学生目睹或体验过教师使用CP(Perappadan 2012)。据《泰晤士报》新闻网(2012年)报道,家长教师协会联合论坛(PTAUF)对孟买60所学校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参与调查的几乎所有教师都以使用尺子打学生或向学生投掷粉笔等方式实施CP。
妇女和儿童发展部(200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印度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中,69%的人认为有可能患CP。此外,调查发现,德里每年有225000多名学生接受CP。超过35%的公立学校学生和31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Current Use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in American Public Schools
Terry L. Ros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
The use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of students in American public schools are
described, A school discipline survey form was mailed to 324 principals in 18
randomly selected states representing the nine U.S. Census districts. Results indicated widespread use of corporal punishment with students at every grade
level in virtually all 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scriptions of the use of corporal punishment across demographic, administrative/procedural, and ad-ministrative opinion variables are provided and discusse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instructional implic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The use of corporal punishment by school personnel as a disciplinary method has persisted for many years (Bolmeier,1976; Freeman, 1966; Manning, 1979;Maurer, 1974; Williams, 1973). At various times, corporal punishment has been either advocated or condemned, and it has been the cause of numerous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issues of ethics, morality, legality, and efficacy (Owens amp; Straus, 1975; Raichle,1977-1978; Reinholz, 1979; Reitman, 1979;Skinner, 1979), Two recent events have returned corporal punishment to the center of educational controversy. First, the U.S. Supreme Court ruled in Ingraham v. Wright(1977) that corporal punishment does not violate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gainst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Second, the recent call for a 'return to basics' in educational and disciplinary practices has been seen by many as an endorsement of corporal punishment in the schools (e.g., Welsh,1978).Proponents suggest that corporal punishment may provide rapid reduction ore limination of the behavior, facilitate dis-crimination learning, and vicariously deter similar misbehavior by peers (e.g., Killory,1974; Mercurio, 1972; Reinholz, 1979).Corporal punishment may also be favored because it is quick, easily available, and apparently effective (Smith, Pollo way, amp; West, 1979). Numerous arguments against the use of corporal punishment have been advanced, including the possibility of (a) the individuals withdrawal from the punishing situation whenever possible (Azrin, Hake, Holz,amp; Hutchinson, 1965; Bongiovanni amp; Hyman,1978); (b) modeling the act of delivering punishment (Bandura, 1965); (c)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punished behavior, which then may be emitted by other students in situations when the teacher is not present(Bandura, 1965); producing negative peer reactions to the child receiving punishment(Sulzer Azaroff amp; Mayer, 1977); (e) an absence of generalization effects to different settings (Birnbrauer, 1968; Bongiovanni,1979; Johnston, 1972; Risley, 1968); and (f)causing aggressive reactions, including both operant aggression (i.e., attacks against the source of the punishment; Delgado, 1963)and elicited aggression (i.e., attacks directed toward other people or property in the environment; Azrin, Hake, amp; Hutchinson,1965; Azrin, Hutchinson, amp; Sallery, 1964;Ulrich amp; Azrin, 1962).Regardless of the position one assumes regarding corporal punishment, it is increasingly clear that most professional and public opinion is shaped more by hunch, folk lore, and conjecture than by empirical evidence. There appear to be no applied empirically based studies that support the use of corporal punishment (Bongiovanni,1979). Rather, it seems that supportive evidence comes from clinical practice (Kil-lory, 1974; Leviton, 1976) or anecdotal field studies (Mercurio, 1972). Published reviews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s of punishment in applied settings are still largely unknown(Bongiovanni, 1979; Gardner, 1969; Johnston, 1972; Solomon, 1964; Walters amp; Gru-sec, 1977).Despite the absence of research support, corporal punishment continues to be used in the public schools (Hyman, 1976; Hyman, McDowell, amp; Raines, 1977; National Coalition of Advocates for Students, 1983). Not only is little known about the effect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but we are also lacking equally in descriptive information regarding its use in public schools.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describe the reported uses of corporal punishment with students in American public schools.
Method.
election of Respondents
Initially, 2 state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each of the nine U.S. Census districts. A total of 10 school district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each of the 18 selected states, using Pattersons American Education(1980). A letter requesting a list of their districts principals and explaining the reasons for the request(i.e., lack of empirical information regarding disciplinary practices combined with the call for a return to basic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actors for future practices) was sent to each superintendent of the 180 selected school districts. Superintendents who did not respond within 2 weeks of the due date selected for their response received either follow-up letters or telephone calls. Usable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from 103 superintendents (57%). Those who declined to participate, had district provisions prohibiting participation, or provided incomplete information were classified as
non usable responses. Finally, school principals from each usable school district response were selected to receive the school discipline survey form. The number of schools selected for each state varied slightly as a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usable responses from the district superintendents. Thus, 324 schools were selected across the 18 preselected states. The schools were controlled for grade level, and all other demographic variables (e.g., size of community, number of students, and sex of principal)were controlled through the random selection process. Special schools (e.g., special education centers or vocational/technical schools) were excluded. Each schools principal received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3202],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