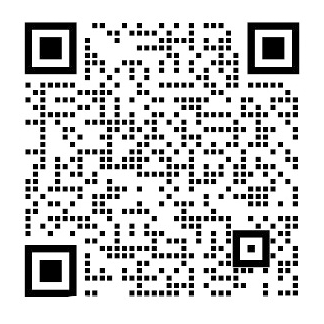伦理之旅:权利、关系和反思
原文作者 Jane Bone 单位 奥克兰科技大学
摘要:本文讨论了用相同的同意书接近三个不同早期儿童的环境的过程。在每个环境中,人们对伦理程序的看法是不同的。这形成了一个发现之旅,并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伦理程序的机会。虽然研究者始终有责任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进行研究,但幼儿教育领域提供了特殊的挑战。在这项研究中,很明显,关于伦理的观点包括权利、关系和反思。让教师和家长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得到了认可。儿童的同意书得以描述,并且随着它成为谈判的焦点,它对研究者态度的影响逐渐成为伦理遭遇的描述。
关键词:伦理;权利;关系反思
将早期儿童的环境作为研究场所,意味着那些进行研究的人的道德实践可以受到审查。 (Aubrey, David, Godfrey amp; Thompson, 2000)。然而,参与这些环境的每个人都在研究过程中发挥作用:儿童和家长、教师、管理人员、把关人和研究人员。研究人员也可能对他们的机构、资助机构或教育部负有义务。如此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关系网中,意味着对道德规范的强调越来越多。在澳大利亚和奥特亚罗亚/新西兰,教育工作者的道德准则工作仍在继续 (Hedges, 2001; Kennedy, 2001)并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讨论道德实践 (Moss, 2001; Smith, 1999)。儿童会自动作为合适的研究对象的想法是一个被质疑的假设 (Cannella, 2002; Christensen amp; James 2000; Fasoli, 2003)。我与儿童同意书的历程包括权利、“关系范式” (King, Henderson amp; Stein, 1999, p. 14)以及关于我自己作为研究者的立场的问题。反思性立场的力量在这一叙述中显而易见,它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
Garbarino讨论了研究过程中和儿童相关的成人取向或 “立场”。他说,有用的伦理思考涉及的问题是 “儿童对隐私有什么权利?对权威有什么权利?对尊重有什么权利?”(Garbarino, Scott amp; Faculty of the Erikson Institute, 1992, p. 16)。在权利方面,《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的一些条款维护了儿童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第12条)和言论自由的权利(第13条)。该文件还维护了父母向儿童提供指导的权利(第14条)(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我的研究是关于幼儿环境中的灵性,是坚定的定性研究,也是公认的敏感课题研究 (Lee, 1993)。事实证明,灵性是一个引起强烈反应的领域,而协商什么、在哪里、如何进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Coady(2001)所指出的,在任何研究中都有关于知情同意、欺骗、保密和隐私的问题。我决定邀请儿童对同意书作出反应,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事实证明,对儿童的这种反应是我自己思想变化的焦点,也是与家长、教师继续对话的地方。
在研究过程的早期,很明显,伦理程序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但除了官方表格本身,还有相当多的信息需要和参与研究的每个人交谈,并在交谈中分享和扩展。其中一项被认为至关重要的要求是“透明度”,该要求在其中一个中心经常被讨论。透明就是“容易看穿、明显、明显、容易理解、不伪装”(《简明牛津词典》)。带着一堆表格来到一个中心是不够的。透明化包括谈话、讨论和解释,而且不仅仅是对家长小组,而是对家长个人,特别是当他们对研究有疑虑时。有时,透明与不尊重研究之间的界限变得相细微,问题也层出不穷。什么时候才是透明的?如果对透明度的要求危及到项目怎么办?什么时候透明会挑战隐私和保密的概念?在这些问题引发的讨论中,新的意义得到了分享,关系得到了加强。以最好的意图进行研究的愿望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紧张在于保持意识,好的意图并不能保证道德的方法。
伦理程序的谈判在三个不同的场合进行,数据收集包括照片和使用录像机。孩子们的同意书提供了关于研究性质的信息,关于我作为研究者的信息,以及涉及父母的信息。当问到问题时,孩子们会在空格里圈出这些字:快乐、好、不确定、担心。同意书包括一个声明,说,“我正在了解灵性,你可能也想了解一下。我不确定如何向你解释灵性这个词。灵性可能是你感觉到的东西,可能是你做的或看到的东西hellip;hellip;”。我从一开始就清楚不知道,这不是隐瞒信息,而是试图诚实地承认不知道是我的出发点。定性研究范式是关于分享出现的意义,而不是证明假说,同意书对此也表达地很清楚。
对透明度的关注也确保了家长和中心之间的伙伴关系得到尊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得到加强。父母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儿童的同意书包括要求父母向他们的孩子宣读,并且有一个空间让孩子签署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和一个空间让父母签署。邀请父母与他们的孩子分享同意过程这一事实提供了保证,许多父母说他们对此表示感谢。
同意书的一个特点是包含了我的照片,我希望这能显示出一些互惠性。这有助于孩子们了解我,而且在家长和孩子们把同意书带回家,看了照片并谈论了我正在做的事情之后,互动关系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我成了一个可以给我讲故事或展示家里东西的人。这让我渡过了“备用部分”的阶段:Sumsion(2003)最初不确定是否加入该中心,他描述了作为一个研究者与儿童互动的复杂性。在几个孩子告诉我他们因为照片而“认识”我之后,我被纳入中心生活的感觉更强烈了。
信息表要求允许收集视觉数据、拍照和使用录像机。家长们与我分享了他们对孩子的视觉图像的担忧,并表明他们担心照片或视频被滥用的可能性。互联网通信和信息共享的便利性使家长们更加意识到这些危险,因此他们放心地知道,获得伦理批准涉及到解决存储问题,而且数据最终会被销毁。一些家长说,“你永远不知道hellip;”,并表明这是一个关切,也是他们不确定的事情,但他们需要感到安全并讨论所有的可能性。
孩子们被问及他们是否希望参与视频的制作。他们是否介意被拍照?同意书明确指出,儿童可以改变他们的想法,特别是关于被纳入视频的问题。当其中一个视频被展示给家长时,有人评论说,如果有一个隐藏的摄像机就好了,因为儿童意识到被拍摄。这再次提供了一个
讨论道德问题的机会,询问家长对更衣室里的隐藏摄像机的感受,足以引起一阵抗议。然后我们谈到了儿童和他们对收集数据的视觉手段的熟悉程度,以及摄像机在该中心的使用。
在这些讨论中,新的意义被构建起来,并共同做出决,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仅仅依靠外部文件和机构来提供有关具体实践的指导是不够的。例如,对幼儿环境的研究者来说,道德准则或机构以道德委员会的形式提供的指导可能是不够的 (Hedges, 2002)。作为一名学生和一名员工,我的道德申请得到了两个委员会的批准。我自己的机构欢迎有机会查看儿童同意书,并承认这是他们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事情。这些都是在儿童早期研究中建立“伦理文化” 的过程中迈出的步伐,它将支持那些希望将幼儿纳入教育研究的研究人员的努力。
相反,依靠个人诚信作为道德的唯一方法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Singer(1993)所指出的,如果涉及自我利益,就必须有保障措施。Singer (1993年, 第35页) 讨论了Naroll的工作,他提出了利用“道德网”的想法。道德网包括“家庭和社区联系,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为每个人的行为提供道德背景”。来自幼儿社区内部以及参与幼儿教育的教师和家庭的压力将确保所有研究人员关注与儿童有关的道德过程。
在研究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或以一种新的、对道德负责的方式研究熟悉的事物时,做出突破性的道德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项研究中,很明显,伦理过程得益于个人对幼儿教育的参与感。正如Coombe和Newman(1997年,第48页)所说,“什么构成了道德行为,是因地制宜的”,在提交儿童同意书的三个环境中,情况当然是如此。
在第一所蒙台梭利学校,中心的所有者和教师对设立这样一个表格的整个想法充满了热情。孩子们的父母说他们很喜欢这一方面的研究,觉得自己很有参与感。我在中心的入口处留了一个邮筒,孩子们把填好的表格寄回来,我把它清空,然后处理疑问和关切。Reggio Emilia的影响在这个中心也很明显,儿童和家长作为“学习者社区”的一部分参与到这个环境中,我也成为这个社区的一员。到目前为止,这个旅程被证明是顺利的,而且这个中心的程序非常成功,我在下一个中心也重复了这个程序,并期待着同样的反应。
第二中心的理念是基于新西兰幼儿课程Te Wh ariki的整体原则(教育部,1996)。儿童同意书被接受为程序的一部分,我非常关心道德程序,而不是中心问题。邮筒很受欢迎,因为它减少了教师的参与,而且孩子们很喜欢它,所以它一直在那里。这个经验促使我思考每个环境中的差异。在这个中心,所有的研究参与者是否都对伦理程序和同意问题感兴趣,以及谁的利益得到了满足,这个问题只是停留在表面。Knight、Bentley、Norton和Dixon(2004年,第391页)指出,围绕同意书的谈判可能变得“不可见、无声和不重要”。由于需要继续进行研究过程,这种抹杀就变得更加容易。旅行中的不舒服或不确定的时刻可以在继续旅行时被抛诸脑后,我已经与另一个中心建立了联系,并渴望继续前进,在第三个环境中开始谈判。
在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案例研究中,当我概述我的伦理计划时,我对伦理和幼儿的思考受到了挑战。当我们讨论儿童将有他们自己的同意书需要签署时,他们远没有受到热情的欢迎,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冷淡。这位华德福(Steiner)幼儿园的老师说,在这种情况下,她是 “最成熟的”,这意味着要对那里发生的事情负责。她觉得家长完全信任她和他们的孩子,因此她是教室里发生的事情的最终仲裁者。与其他中心一样,很明显,如果她决定支持这项研究,家长就会同意。在她看来,让孩子们知道我的研究计划是不可接受的,因他们属于成人世界,而孩子们是作为儿童来到她的幼儿园的,她为他们创造并维持这个空间。当我提到在其他中心,孩子们甚至鼓励他们的父母归还表格并把它们贴在盒子里时,她不认为这是个意外。事实上,这以一种我无意的方式支持了她的观点,而且很明显,我的计划体现了斯坦纳哲学认为有问题的那种角色反转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意识,即代表儿童做决定是道德实践;教师必须准备好承担这一责任,并认识到在斯坦纳教育中,“儿童对成人中最深层的道德力量,对仁慈和敬畏的品质有最大的呼唤” (Edmunds, 1992, p. 34)。我们的对话和我“随波逐流”的决定成为了一个转折点,因为我意识到,在每个获得同意和道德认可的环境中,蕴含着多少权力和控制。Knight等人(2004年,第402页)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建立信任和可信度是具有挑战性的,在他们对同意书的探索中,他们注意到在研究发生的社区中可能存在“冲突的叙述”。在这种情况下,“冲突的叙述”(Knight et al. 2004, p. 402)
迫使我放慢脚步,重新评估我的立场。我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在这种环境下,为相互理解而进行的斗争将决定我的关系,而我们继续一起旅行的基本因素是信任。
合作和建立关系的愿望构建了Guillemin和Gillam(2004年,第265页)所说的 '伦理上的重要时刻'。在承认我自己的研究议程的同时,尊重每个环境中的差异,有时是一种困难的平衡。对我自己的立场提出质疑的过程承认了Guillemin和Gillam(2004年,第274页)所说的“贯穿于研究的每个阶段”的反思性,这也包括伦理过程。当我开车离开会议时,我想知道。我的立场是什么?我是否承诺得太多了?是否有空间容纳我和我的问题?我的热情会被分享吗?带着这最后一个问题,我又回到了我的研究的核心,它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我珍视我在这个中心的关系,不得不放下短暂但强大的想法,即不知何故我的儿童同意书是包容和不可抗拒的。必须认识到自满是危险的,占据一个舒适的地方就是不承担风险,也不参与蕴含在关系中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可逆转的和不稳定的”(福柯,1994年,第292页)。在变化的地面上的感觉是旅程的一部分。一个有效的、有道德的研究者必然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有义务遵守迄今为止所讨论的伦理原则,而且要关注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对这些原则的不断发展的理解”(Snook,2003年,第165页)。当研究程序与构成幼儿教育的多种声音交织在一起时,伦理过程突出了社区内的紧张关系。
谁的声音被倾听,谁觉得自己可以说话,谁保持沉默,这个问题让我感到不安 (MacNaughton, 2003; Viruru, 2002)。我想知道,在伦理学表格的官方语言中,我的声音是怎么回事。这确实是一个必须个性化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处理我的伦理学申请的机构不熟悉儿童同意书,这份同意书仍然是“用户友好”:它被构建成一个小册子,包括一张照片,并为儿童提供重新审视其决定的机会。由于语言对伦理委员会来说不够“正式”,信息表不得不被修改。这不是批评,而是承认大学伦理委员会所要求的文书工作是必要的,但也是正式的,与通常发给家长的通讯和通知不同。Knight等人(2004)讨论了语言的问题性,这些语言可能满足伦理委员会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可能参与研究的社区。对程序的不同态度给了我一种不稳定的感觉。我质疑,在构建同意书的过程中,谁的声音被赋予了特权。是伦理委员会、我自己、孩子、老师还是家长?
笑声平衡了其中一些道德考虑的严肃性。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填写表格的邮筒到来。他们用金毛笔和闪光笔填写了他们的同意书,其他的孩子在上面涂涂画画,有的孩子则在上面画起了思考的圆圈。许多家长说他们很喜欢把表格读给他们的孩子听,并记录下他们的回答。有一个孩子在完成表格的第二天就来给我讲一个很长很复杂的鬼故事。他把我们都吸引住了,然后开始大笑,显然他觉得调查灵性的整个过程有点像一个笑话。
在认识到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英语原文共 24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3196],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