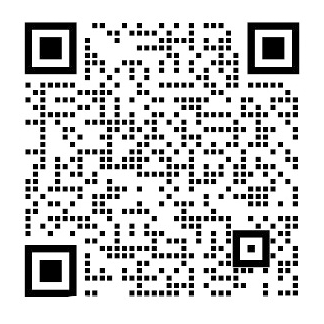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对积极和消极情绪的共情
摘 要 社交焦虑障碍(SAD)与积极情感体验的增加和减少有关。然而,对于悲伤的个体如何感知和对他人自然流露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即认知同理心和情感同理心,人们知之甚少。在本研究中,具有广义SAD(n=32)和人口统计匹配的健康对照HC(n=32)的参与者完成了行为移情任务。认知同理心是通过目标和参与者对目标情绪的持续评分间的相关性来建立的,而情感同理心是通过目标和参与者对情绪的持续自我评分间的相关性来建立的。患有SAD的人与HC的区别仅仅在于积极的情感同理心:他们不太能够代替他人分享他人的积极情绪。调查研究显示,悲伤患者的情绪不明朗和消极的人际关系感知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未来需要使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以检验这一发现是否代表无法或不愿分享积极影响。
关键词 同理心 社交焦虑障碍 影响共享
1 引言
社交焦虑障碍(SAD)的特征是对社交场合的持续和不成比例的恐惧,导致在这种情况下避免或强烈的不适(AmericanPsychiatricAssociation,2013)。大量文献已记录了SAD患者负面影响水平的升高(Farmeramp;Kashdan,2014;Hofmann,2007;Watson,Clark,amp;Carey,1988),越来越多文献表明,与SAD相关的非典型情感功能也包括低水平的积极情感(Brown,Chorpita,amp;Barlow,1998;Hughesetal.,2006;Kashdan,2007;Watsonetal.,1988)。然而,与我们对悲伤个体情感体验的理解相反,我们对悲伤个体如何感知和对他人的积极和消极情绪做出情感反应知之甚少,这是一种被称为移情的社会认知形式。我们对悲伤的认识上的这种差距是不足的,因为一个人对他人的感知和情感反应方式对他或她的社会功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Eisenbergamp;Miller,1987;Zakiamp;Ochsner,2012);我们知道SAD的特征是明显的社交障碍。(forreview,seeAldenamp;Taylor,2004)患有SAD的人朋友更少,恋爱和性关系更少,结婚的可能性也比一般人群更低,甚至比患有其他焦虑症的人更低。考虑到这些人际关系上的困难,我们有理由认为患有SAD的人可能会经历失调的共情功能。事实上,同理心的困难可能是一种诊断机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些心理健康状况中的社会损害。
1.1 同理心
大多数理论认为共情包括认知和情感两部分(e.g.,Davis,1994;Wispe,1986;Zakiamp;Ochsner,2011)。认知同理心,又称心智化,是指对他人情绪状态的准确感知;而情感同理心,又称经验分享,是指以相同的情绪对他人情绪状态进行替代情感反应(Gladstein,1983;Zakiamp;Ochsner,2012)。还有许多其他与同理心相关的概念,我们目前不会考虑研究。与情感体验一样,同理心也可以根据效价来区分。负同理心即理解或分享他人的消极情绪状态,可以与较少研究的正同理心,即或理解或分享他人的积极情绪形成对比(seeMorelli,Lieberman,amp;Zaki,2015)。与消极和积极情感的构念类似,消极和积极同理心之间存在中度正相关(Morelli,Lee,Arnn,amp;Zaki,2015;Sallquistetal.,2009),例如,在夫妻中,接受积极同理心比接受消极同理心与关系幸福感的关系更强(Gable,Gonzaga,amp;Strachman,2006)。
1.2 悲伤中的认知和情感同理心
迄今为止,有一项研究明确地考察了社交焦虑与认知同理心之间的关系,并从相关研究中进一步推断出SAD患者的认知同理心。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一个未被选择的本科生样本被要求对描述社会排斥和包容实例的录像目标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事后评级(Auyeungamp;Alden,2016)。当参与者面对社会的威胁时会产生更大的社会焦虑与增强认知移情,但是当参与者没有面对社会的威胁就没有联系社会焦虑和认知移情,也没有对以社会焦虑和认知移情为目标进行描述。另一项高度相关的研究检验了心智理论,即准确推断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一些人认为这等同于认知同理心(Blair,2005)。当被要求仅用眼睛作为刺激来识别情绪时,悲伤的参与者比对照组更容易识别消极情绪(e.g.,sad,angry;Hezelamp;McNally,2014)。然而,在对积极或中性情绪进行分类的准确性上,或在确定所描绘的情绪的效价方面(否定,中性,肯定)没有差异。在第二项任务中,涉及回答多项选择题,涉及短片中人物所经历的情绪的原因和性质。与健康对照组的参与者相比,悲伤组的参与者更倾向于做出错误的选择。患有SAD的参与者所选择的回答表明,他们倾向于过度理论化他人情绪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包含的推论超出了所呈现内容的合理范围。与认知同理心相关的还有对人际情感知识的研究,即识别他人情感以及理解其原因和后果的能力(Eisenberg,Hofer,amp;Vaughan,2007)。在SAD中,人们对情感同理心的了解甚至比认知同理心更少。在未经选择的大学生样本中,自我报告倾向于别人的同情和关心的感觉经验表现出一个小正相关,社会焦虑(femalesr=0.12,malesr=0.14;Davis,1983)。Samson,Lackner,Weiss,andPapousek(2012)在一项更近期的研究中,也在一个未被选择的样本中发现,社交焦虑与需要心智推断理论的卡通片的幽默感呈负相关,但与不需要心智推断理论的卡通片无关。作者认为,这可能表明缺乏积极的情感分享(表明积极的情感同理心较低),或漫画中对演员的同理心增加,从而导致消极情感增加(表明消极情感同理心增加),并降低了幽默。或者,这些结果可以用认知同理心的中断来解释。这些关于社交焦虑和同理心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提示,悲伤个体可能比低焦虑个体更善于将他人的消极情绪状态作为与社会排斥经历相关的心理状态(Auyeungamp;Alden,2016);然而,也有证据表明,社交焦虑可能与对他人情绪状态的心智化困难有关,尤其是在识别复杂而非简单的情绪时(OTooleetal.,2013)。我们的推论也是有限的,因为这些研究大多使用静态的、阶段性的刺激(如面部表情的图片),而且都使用离散的反应选项(如多项选择)。在情感同理心方面,在SAD中,积极的情感同理心可能受到损害,消极的情感同理心可能得到促进。然而,这些假设仅基于三项在非临床样本中进行的研究,并且受到与认知同理心相同的因素的限制,即静态刺激和离散反应选项。我们需要的是在其他人自然展开的情绪的背景下,直接检查患有SAD的个体的认知和情感同理心。
1.3 目前的研究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悲伤个体的认知同理心和情感同理心与匹配的、非焦虑的健康对照参与者(HCs)进行比较。我们使用改编版的共情准确性任务(Zaki,Bolger,amp;Ochsner,2008)来评估共情,其中参与者观看不同个体的简短电影剪辑(例如,讨论消极和积极的情绪状况。在每一段影片剪辑中,参与者被要求不断地对目标情绪或他/她自己情绪的情绪价进行评分。认知同理心是由目标和参与者对目标情绪的评价间的一致性程度推断出来的(Zakietal.,2008)。采用类似的方法,我们试图通过检查目标的自我情绪评价和参与者的自我情绪评价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来提供情感同理心的第一个行为指标。根据之前的文献,我们预计相对于HCs,SAD个体的认知同理心没有差异,但是负性情感同理心会更一致,而正性情感同理心会更不一致。我们还试图探索为什么同理心会产生差异。有许多潜在的机制可以解释群体同理心的差异。鉴于目前的研究数据收集的一部分,正念减压(Goldinetal.,2016)和更大的认知行为治疗研究团体相比,,我们从这个数据库选择了三个理论推导被试变量,探索机制之间悲伤和共情的关系。第一个是情感体验,自我报告的同理心与每日积极和消极情绪水平呈正相关(Nezlek,Feist,Wilson,amp;Plesko,2001)。第二个潜在变量是情绪知识,比如识别自己情绪的能力(Jonasonamp;Krause,2013)。社交焦虑与情绪知识呈负相关,具体表现为关注自己情绪的倾向和描述自己情绪的能力(e.g.,Davilaamp;Beck,2002;Turk,Heimberg,Luterek,Mennin,amp;Fresco,2005)。因此,在SAD中任何同理心的损伤都可以用这些因素来解释。与同理心有关的第三个变量是人际感知。对目标的正面认知,例如对目标的更大相似性或亲和力的感知,可能会激发一个人试图理解目标的视角,并可能会增加一个人对目标视角的重视。尽管在非自我相关情境下的人际认知在SAD中研究较少(forreview,seeAldenamp;Taylor,2004),但有一些证据表明社交焦虑与他人的负面认知相关(Jonesamp;Briggs,1984;Leary,Kowalski,amp;Campbell,1988)。因此,这也可以解释任何观察到的与悲伤相关的同理心差异。
2 方法
2.1 参与者
研究对象为32名SAD患者和32名HC患者。患有SAD的参与者是随机对照试验(RCT)的一部分,该试验比较了认知行为疗法、正念减压疗法(MBSR)和等待控制条件(Goldinetal.,2016)。最终的RCT样本包括108名符合DSM-IV终生版焦虑障碍访谈计划(ADIS-IV-L;DiNardo,Brown,amp;Barlow,1994)的被试。根据与其中一个HC的匹配程度,选择SAD参与者进行当前的分析。HC的纳入和排除标准与SAD患者相同(见下文),进行采访确认他们没有任何当前或过去的精神疾病。在招募的37名HC中,有3人由于参与者或计算机错误,没有可用的数据来完成移情任务。HCs的两名参与者在他们的年龄阶段五年内没有进行过悲伤的参与者匹配,因此没有被纳入当前的研究中,因此每组最终有32个样本。患有SAD的参与者免费接受治疗,而HC的参与者则因参与治疗而获得适度的经济补偿。所有参与者均按照斯坦福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规定提供知情同意。所有参与者要求年龄为21~55岁,英语流利,右利手,非色盲,通过磁共振成像(MRI)安全筛查,无当前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病史、头部创伤、神经系统疾病和重大学习障碍。患有SAD的参与者也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之前完成了6次或更多的CBT课程,或者参加了MBSR课程,参加了正式的冥想静修,或者进行了定期的冥想练习。除了继发性的广泛性焦虑障碍、特殊恐惧症、强迫症、恐慌症、重度抑郁症和心境恶劣症外,他们还被排除在精神障碍之外。
表1提供了这两个样本的人口统计信息。患有SAD的参与者在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或种族方面与对照组的参与者没有差异。正如所料,他们报告的社交焦虑程度明显更高。
2.2 访谈和自我报告测量
焦虑障碍访谈计划DSM-IV(ADIS-IV-L;DiNardoetal.,1994)是一个用于诊断焦虑症和相关疾病的半结构化访谈(Brown,DiNardo,Lehman,amp;Campbell,2001)。在一系列的焦虑症患者的样本,具有优良的信度(k=0.77,Brownetal.,2001)。在本研究中,adi-iv-l由主试管理,主试按照Brown等人(2001)提出的标准进行培训。为了评估评估者之间的可信度,我们让临床心理学博士和博士生对20%的访谈进行了回顾。
利博维茨社会焦虑量表-自我报告版本(LSAS-SR;Frescoetal.,2001;Liebowitz,1987;Rytwinskietal.,2009)评估了对一系列社会互动和表现情境的恐惧和回避。在过去一周的24种情况中,参与者对每种情况下的恐惧程度和回避频率进行了2个4分制量表评分,范围从0(无/从未)到3(严重/通常)。这些例子包括“参加派对”、“在会议上发言”和“抗拒高压销售人员”。总分是24个恐惧等级和24个回避等级的总和。LSAS-SR显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0.95)和良好的区分效度(e.g.,Frescoetal.,2001)。信度在目前样品还好(HC=0.87,悲伤=0.92)。
积极和消极影响时间表(PANAS;Watson,Clark,amp;Tellegen,1988)是一个20个项目的问卷,包括两个10个项目的量表,由描述感觉或情绪的单词组成,从1(非常轻微或根本没有)到5(非常)。参与者被要求根据“你在过去一周的这种感觉程度”完成这些评分。一种量表衡量积极影响(PA;样本项目:“热情”、“感兴趣”和“自豪”,而其他衡量消极影响的指标(NA;例如:“内疚”、“易怒”和“害怕”)。在大学生样本中测量表明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度(r=0.76;Watsonetal.,1988),和良好的内部一致性。(a=0.75and0.86forPAandNA,respectively;Mackinnonetal.,1999)。在当前示例中,它还展示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PAscale:HCa=0.89,SADa=0.89;NAscale:HCa=0.82,SADa=0.90)。
自己的情感知识,特别是倾向参加一个人的情绪(注意情感)和能力来识别自己的情绪(情绪的清晰度),评估了23-item规模Palmieri,Boden,andBerenbaum(2009)使用多维标度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项目从多伦多述情障碍Scale-20(TAS;Bagby,Parker,amp;Taylor,1994)和特征Met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英语原文共 11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7494],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