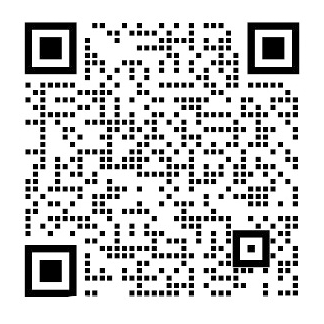五四运动的重新定义
原文作者 Joseph T. Chen
单位 加州圣费尔南多谷州立学院历史系
摘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然而,学界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似乎并不清晰,有许多学者将二者认识为一个事物,这显然并不正确。本文将通过分析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区别,梳理清楚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Ⅰ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近代革命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共和国革命后的一个新阶段。它既是反帝国主义的,也是反军阀的,代表了中国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新的动荡力量的反应。1919年5月4日,为了特别抗议中国宣布的《凡尔赛和约》条款,以及日本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条款,大批学生在北京举行示威活动,谴责亲日的北京政府。这股革命浪潮很快在全中国迅速蔓延,带动了群众意识的迅速增长和文化变革,并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达到高潮。五四运动的重要性及其产生的各种影响和后果,使得五四运动本身的界定、传播和评价问题复杂化,对其真实性质和特点的界定,对其实际领导人的明确认定,以及对其范围和成就的现实评价,都成为有争议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承诺、政治关系或者职业利益常常蒙蔽了研究这一运动的个人的客观性,因此也蒙蔽了他们对这一运动的理解。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试图澄清关于运动性质的某些观点,并建立一个基础,据此,MFM[1](五四运动)既不能被理解为与新文化运动(NCM[2])相同,也不能像一些共产主义作家所指称的那样,被俄国革命所鼓舞,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相反,它主要是一个爱国的抗议运动。中国人对于直接的政治行动,以及在与新文化思想运动的合作中,对于古老中国传统的最终解决和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诞生,起到了极为宝贵的作用。
Ⅱ
我相信,把五四运动误解为新文化运动的同义词,始于对五四运动最早的自由主义或独立观点,或至少是五四运动的文化方面,作为一种“中国文艺复兴”。 早在1995年,上海著名记者黄元勇就开始推动一种新文学,这种新文学将“使中国思想与当代世界思想直接接触,从而加速中国文学的根本觉醒”。这种按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国文学的想法很快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随后,他们努力采用白话文写作,将西方思想介绍给中国,逐渐促进了全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不久,中国出版的新书、翻译和期刊迅速增加,中国青年对新思想和新观念的热情也日益高涨。到了1919年,中国的文艺复兴才真正开始。
然而,这一时期文化和社会变革的重大现象发生在五四事件发生之前。当学者们后来提到这个现象时,很明显他们并不是在讨论五四运动,而是新文化运动,它拒绝了古老的中国传统,而是支持现代西方思想。 因此,新文化运动主要是文化的内容,“思想”导向而不是“行动”导向。
“五四运动”一词在五四事件后不久首次在学生和新闻界使用,仅用于一系列政治行动,例如5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罢课和紧接着五四事件之后的全国性事件,最显著的是抵制日货、总罢工和拒绝在凡尔赛签署和平条约。从那时起,“五四运动”一词几乎与“五四事件”一词可以互换。直到后来,这个词才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含义。 因此,例如,作者李长之[3],写于1944年,开始认为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发生在5月4日的民众抗议,而且是一个“中国与西方文明接触所产生的文化过程”。鲍增鹏[4]在论述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时认为,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的本质与中国青年运动的本质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他说这场运动:
“hellip;hellip;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商人罢工、工人罢工、抵制日本以及其他新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受到二十一条和山东决议后的爱国主义情绪的启发,受到西学精神和用科学和民主重新评价传统的愿望的启发,以建设一个新中国。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或组织良好的运动,而是一系列活动的结合,这些活动往往有不同的想法,但也不是没有主要的潮流。”
周士心认为这场运动是“近代中国的一场知识分子革命”。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虽然不像李、鲍、周那样包罗万象,但他们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义,但对五四运动的解释却颇为客观。 李大钊,在“五四”事件几个月后写道,这是一场“反大亚主义、反侵略、不恨日本”的爱国运动。陈独秀在1938年写道,开始把五四运动视为“民主革命的整个时代”的相关事件之一,“民主革命的整个时代”始于“九二”共和革命,至今仍在继续。
毛在第一次论及五四运动运动时,似乎对五四运动运动有了更好的理解。1939年关于五四运动运动的著述,与钱、李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表现之一,是超越1992年辛亥革命的明确步骤。他指出,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中国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结合。然而,他并没有试图将五四运动等同于新文化运动,而是指出,五四运动后来转变为一场文化改革运动。
一年后,毛在他的论文《新民主主义》中详细阐述了这一主题,并明确阐述了这场运动的共产主义版本。 他指出,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这场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五四运动前八十年)和“新民主”(五四运动后二十年)之间的分界线。他的原因如下:
- 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袖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 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革命,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人不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的无产阶级。
- 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间的斗争。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诞生了一股全新的文化力量——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知识只对资产阶级有用,因而被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所取代。
但是毛泽东想给予应有的赞誉。他承认,这场新的文化大革命是五四运动的产物。
共产党历史学家华康似乎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场运动。华认为,五四运动运动不应被视为一场纯粹的文学革命,因为将其视为一场文学革命,反映了蓄意贬低其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意图。相反,他选择通过明确区分他所谓的“五四群众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来展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相互关系。他写道:
五四群众运动使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范围得到了扩大和深化。它将纯粹的“五四”前的文化运动转化为群众运动,使其在第一时期与民族解放的群众运动相融合。就这样,在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提供了自我觉醒并导致思想解放的条件,而五四运动则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个群众基础。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够对中国近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与社会主义观点相反,以孙中山、蒋介石和胡适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动向观点,并不强调阶级路线。虽然毛并没有将五四运动等同于新文化运动,但他从一开始就把这场运动看作是学生的爱国运动,是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和知识分子运动有着密切联系的运动。他注意到:
在北大学生发起五四运动后,所有的爱国青年都认识到知识改革是为未来的改革活动做准备。(新文化运动导致)民意发展迅速,声势浩大,全国学生罢课事件层出不穷,几乎每个人都以觉醒的意识和决心参加了爱国活动。
然而,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支持显然纯粹是出于政治原因。一方面,他意识到他的政党已经在政治上无能为力,急需振兴。可以招募五四爱国青年为他的无能党建立新的权力基础。 除了这些考虑,他实际上保留评论的优点运动,直到1924年时,(同年)由于他衷心不赞成同年的学生罢工,他几乎颠覆了他的支持五四运动。因此,他对学生在运动中的角色的看法与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蒋介石的个人观点符合他正统的中国传统教育,与新的思想潮流相去甚远。的确,在1927年北伐取得成功之前,他一直遵循着孙中山支持五四运动的政策。然而,蒋介石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反对军阀主义,特别是反对大国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44年的《中国的命运》一书中,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对1915年以来日本所遭受的一系列国家屈辱的回应。他说,五四学生运动是中国人民的强烈要求革命,并摧毁政治制度的军国主义者和官僚。他指出,国民党随后的国民革命实际上是遵循五四的精神,为根除军阀主义和废除不平等的条约而斗争。
但是他对五四运动的认可并不意味着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认可。 作为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蒋介石不喜欢这种打破旧习的新思潮,后来严厉批评了新思潮和学生运动。他攻击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他们要么不尊重中国传统文明,使中国人民失去民族自尊和自信,要么盲目崇拜与中国传统不相容的外来思想。他暗示新文化运动是“对西方文学的零碎介绍”,“对旧伦理的颠覆和对民族历史的排斥”,“对个人解放的要求和对民族和社会的无知”,“对所有纪律的破坏和个人自由的扩张”,以及“对外国的盲目崇拜和对外国文明的盲目引进和接受”。
蒋介石还指责知识分子改革者教导青年人违反道德原则、法律和政府命令,从而腐蚀青年,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孙中山对1924年的看法。从1930年代到近年(特别是鉴于最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大陆的破坏性),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不断推行美化中华民族遗产、维护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传统主义政策。他赞同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拒绝 新文化运动破坏传统的方面。
胡适,文学改革的倡导者之一,认识到学生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角色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反对将后者包括在五四运动一词中的解释。实际上,他同意蒋介石的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是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也接受孙的观点,强调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意义,而不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孙中山对新思潮的评价可能高于一切,而胡适则对新文学运动给予了更多关注。
Ⅲ
尽管这些作者有权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定义这场运动,但他们的分析似乎包含了几个基本的谬误。首先,在他们试图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间建立一种适当的关系时,一些学者似乎没有基本区分每一个运动实际上是什么,以前是什么,以及后来变成什么。很明显,从他们的历史角度来看,五四事件之前发生的事情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早期阶段,五四运动事件之后发生的事情显然是第二阶段或者说是最后一次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分为前五四新文化时期和后五四新文化时期。
其次,一些学者似乎也没有把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全面的抗议运动进行基本区分。当他们提到五四运动一词时,有些人实际上指的是北京五四运动,而不是整个五四运动。但是我们知道,北京五四运动只是整个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三,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中国和西方学术界都有一种不幸的倾向,认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或者至少与其文化方面是一致的。一些学者甚至强调了整个运动的“知识分子”方面,而忽视或轻视了运动的“大众化”方面。虽然在这里我并不主张运动的大众方面比知识方面更重要,但我确实相信大众方面和知识方面一样重要。作者对上海五四运动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上海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对中国所有社会阶层的共同努力的回报,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努力。如果过分强调这场运动的“知识分子”一面,忽视这场运动的“大众”一面,那么这场运动的真正本质就被扭曲了。
但在我们的调查中有几个问题是基本的:(1)这个运动应该被解释为一个单独的事件还是一个持续了几年的事件的发展?(2)五四运动一词是否应该包括,一方面,人民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另一方面,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开始于1917年,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是不同的?(3)这场运动的真正的领导人是谁?
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这个运动应该主要作为一个单独的事件来研究。 也就是说,这个词应该只适用于5月4日在北京的罢课,以及紧接着事件发生并以中国在6月9日至9日拒绝签署和平条约而结束的全国性事件。这一定义符合当时主要参与者的精神,也符合“五四”事变后不久学生和新闻界首次提出的“五四”概念。众所周知,此举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 抗议北京军阀政府的叛国行为,日本政府的掠夺性图谋,以及外国列强在和平会议上对中国的不公正待遇。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一旦在7月实现(惩罚三个“叛徒” ,并拒绝在凡尔赛签署和平条约),全国抗议运动就迅速平息下来。 因此,五四运动不应该被解释为一个持续了几年的过渡阶段。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是否定的。 我承认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影响发生在多边投资基金会之前确实作为一个主要的促进因素,中国人民在五四时期的普遍觉醒,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也带来了扩大和深化的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范围。然而,这两种不同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 不仅每个运动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独特的特点也使得这两个运动截然不同。
首先,五四事件本身肯定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引起或与之有关,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在中国令人窒息的环境和外国侵略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糟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导致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促使中国的主要知识分子寻找拯救中国的答案。然而,前五四运动时期的这些领导人认为,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Redefined
BY JOSEPH T. CHEN
Ⅰ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was an epochal eve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modern revolutionary era, and a new stage after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of 1911 . It was both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warlord, and represented the reac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the turbulent new forces unleashed by the First World War. In specific protest against the terms of the Versailles Peace Treaty as they affected China, and against the terms of Japans infamous Twenty-one Demands, hug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were held in Peking on 4 May 1919 to denounce the pro-Japanese Peking government. This revolutionary tide soon spread rapidly through- out China, spearheading a rapid growth of mass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change, and culminating in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1921, in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Kuomintang in 1921,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nited front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is the very importanc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FM) as well as its manifold repercussions and ramifications, which have complicated the problems of defining, interpreting, and evaluating the movement per se. The definition of its true nature and character, the clear identification of its actual leadership, and the realistic appraisal of its scope and achievements have all become matters of dispute. Ideological commitment, political ties, or professional interest have too often clouded the objectivity of individuals who have studied the movement and hence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it.
In this paper I shall try to clarify certain points of view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movement and to establish a basis upon which the MFM may be understood as neither the same as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NCM), nor, as alleged by some of the Communist writers, a movement inspired b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d by the Communist intelligentsia. Rather, it is primarily a patriotic protest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direct political action, and in its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ew cultural thought movement, rendered an invaluable service to the final dissolution of old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birth of a true Chinese nation.
Ⅱ
The misconception of the MFM as synonymous with the NCM began, I believe, with the earliest liberal or independent view of the MFM, or at least the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MFM, as a Chinese Renaissance. As early as 1915 a leading Shanghai journalist, Huang Yuan-yung, had begun efforts to promote a new literature which would bring Chinese thought into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contemporary thought of the world, thereby to accelerate its radical awakening. This idea of reform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accordance with Western models soon received favourable responses from Chinas leading young intellectuals men like Chen Tu-hsiu, Li Ta-chao, and Hu Shih. Their subsequent efforts to bring about the adoption of the vernacular in writing, and to introduce Western thought to China, had gradually brought about great advances in 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ll over the country. Soon there was a rapid expansion of Chinese publications of new books, translations and periodicals, and a growing enthusiasm for new thoughts and new ideas among the Chinese youth. By 1919 a Chinese Renaissance was truly in the making.
However, this significant phenomenon of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is period took place prior to the occurrence of the May Fourth Incident. When the scholars later referred to this phenomenon, clearly they were not really discussing the MFM, but the NCM, which rejected old Chinese tradition in favour of modern Western thought. The NCM therefore was primarily cultural in content, thought oriented rather than action oriented.
The term May Fourth Movement first came into use with the students and the press shortly after the May Fourth Incident (MFI) and was applied only to a series of political actions, such as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 in Peking on 4 May and the associated nation-wide events which immediately followed the Incident-most notably the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the general strikes, and the refusal of the signing of the Peace Treaty at Versailles. . Since then the term May Fourth Movement has become almost interchangeable with the term May Fourth Incident. Only in later years did the term gradually acquire a broader meaning. Thus, for example, author Ii Chang-chih,8 writing in I944, came to regard the movement not merely as a popular protest which took place on the fourth day of May, but also as a cultural process resulting from Chinas contact with Western civilization. He viewed the MFI as but a signal in this process. Pao Tsun-peng, writing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youth movement, consider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MFM was the same as the NCM. In his opinion, the MFM was but a passing stage in the entire NCM. Chow Tse-tsung, writing on this subject, defined the movement in a far broader sense. He said the movement was:
. . . a complicated phenomenon including the new thought tide,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the student movement, the merchants and the workers strikes, and the boycott against Japan, as well as other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new intellectuals, all inspired by the patriotic sentiments after the Twenty-one Demands and the Shantung resolution, and by the spirit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desire to re-evaluate tradition in the light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China. It was not a uniform or well-organized movement, but rather a coalescence of a number of activities often with divergent ideas, though not without its main currents.
Chow regarded the movement as an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Not quite as all-embracing as Li, Pao and Chow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4680],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