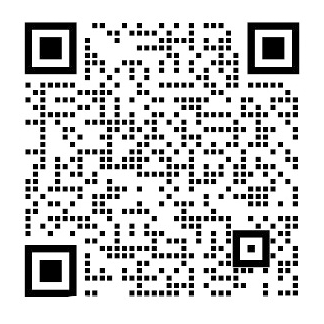权威型、权威型、放纵型、忽视型家庭中青少年适应与胜任力的超时间变化
来自权威、威权、放纵和忽视家庭的青少年适应和能力随时间的变化。儿童发展,1994年,65754-770。在以前的一份报告中,我们证明了青少年的适应能力因父母的方式(例如,权威、专制、放纵、忽视)而异。1987年,一个民族和社会经济异质性样本的约2300 14-18岁的OIds提供的信息用于分类青少年的家庭分为4个育儿风格的群体之一。那一年,又过了1年,同学们完成了电池标准化仪表的攻丝作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父母教养方式变化相关的适应差异要么保持不变,要么增加。然而,虽然权威养育的好处主要是在维持以前的高水平的调整,忽视养育的有害后果继续积累。
在实践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影响提供了权威的家庭得分高于他们的帐篷证明父母的温暖,从权威,纵容,或纪律,非惩罚性的惩罚在各种各样的措施实践上的愉快的家,和在能力,成就,社会发展的孩子抚养方面的一致性每个与积极的发展,自我感觉,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结果(Maccobyamp;(Maccobyamp;Martin,1983)。青少年被称为“权威型”父母,其发展包括学业成就、父母身份的几种典型类型、心理社会发展、戴安娜鲍姆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心理症状(例如,多恩布什、里特、利德曼、罗伯茨和弗莱,1987年;兰伯恩、蒙茨、斯坦伯格和多恩布什,1991年;斯坦伯格、埃尔门和蒙茨,1989年;斯坦伯格、兰伯恩、多恩布什和达林,1992年;斯坦伯格、蒙茨、兰伯恩和多恩布什,1991年),这些报告发现青少年喜欢他们年轻的孩子。
在先前的一份报告(Lamborn等人,1991年)中,我们提供了证据,证明在父母社会化和青少年适应的研究中,基于Baumrind的框架,由Maccoby和Martin(1983年)提出的四重父母类型。在早期的研究中,根据青少年对父母在两个方面的评价,即接受/参与和严格/监督,将大约4个14-i8岁的家庭划分为四个群体之一(权威、专制、纵容或疏忽)。对青少年在四种结果方面的得分进行分析——心理社会发展、学习成绩、内化的痛苦和问题行为——表明,青少年与权威的、专制的、放纵的和疏忽的家庭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具体而言,根据大多数调整指数,来自权威家庭的青少年得分最高,而来自疏忽家庭的青少年得分最低。在专制或纵容群体中,青少年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来自威权家庭的青少年在学习成绩和越轨方面的得分相当好,但在自力更生和自我观念方面相对较差;来自放纵家庭的青少年在参与学校、吸毒和酗酒以及在社会能力和自信等方面的得分相对较差。一般来说,这些模式并不因年龄、性别、种族或家庭背景而有所变化。
本文提供了这些青少年一年后的随访数据。短期纵向随访很重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尽管上篇文章中所报道的跨部门研究结果与其他有关青少年社会化的研究和理论是一致的,但青少年行为和育儿习惯之间所观察到的相关性可能是由于年轻人对其父母的影响,而不是相反的影响(例如Bell,1968年)。虽然有些特定的从这一因果框架中难以分析调查结果(例如,很难想象父母对青少年吸毒的反应会更放纵),许多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父母对高成就的反应具有权威性是很有道理的)。的确,Steinberg等人。据1989年报道,青少年早期的社会心理成熟可能会唤起父母的温暖,而不是相反。短期纵向设计可以对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进行更仔细的评估,尽管这种评估还不够完善。其次,正如本文后面几节所阐明的,此处采用的短期纵向设计有助于反驳这样的说法,即青少年的调整和养育做法之间的联系是由第三个变量造成的,或是由于共同来源或方法上的差异,这是对社会化研究的一种常见的批评,使用了调查数据(在本研究中,父母的分类和青少年调整的评估都来自青少年报告)。具体而言,通过将青少年最初的调整分数作为协变量进行分析,以预测他们在日后对父母的行为的调整,我们极大地减少了调整和养育措施之间的共同方法和来源差异。
使用这种同意程序既有成本也有好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们从一个更具代表性的青少年群体中得到了回应,其中包括那些父母没有上学的青少年。然而,从消极的一面来看,我们的同意程序不允许我们从同等代表性的父母那里获得信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研究局限于自愿参与此类研究的健康父母,而是选择从青少年自己那里收集有关养育方式的信息。
教养方式。父母教养方式指数的制定,以接近鲍姆林德(1971年)和马科比和马丁(1983年)提出的分类方案。第一年的调查问卷中包含了从现有措施中采取或修改的有关养育子女做法的许多项目(例如,Dornbusch、Carlsmith、Bushwall、Ritter、Liederman、Hastork和Gross,1985年;Patterson amp; Stouthamer-Loeber,1984年;Rodgers,1966年)或为工作方案制定的。(鉴于其他研究[例如Hetherington等人,1992年]表明类似的养育措施1年稳定性系数很高,在一年的后续行动中没有重复这些问题。)在双亲家庭中,青少年完成了对父母双方的这些措施(对父母的平均评分),对单亲家庭的母亲则完成了这些措施。(Baumrind[1991]有报道称,父母对孩子的评价相当接近。)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斯坦伯格。(1989年),选择了一些与早期研究中确定的养育方式的若干方面相对应的项目,对这些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了斜向旋转的方法(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维度是正交的)。与其他有关父母教养实践的研究一样(见Schaefer,1965年;Steinberg,1990),三个因素出现了:接纳/参与、严格/监督和心理自治。
我们先前的工作表明,心理自主维度在界定权威性方面很重要,但在区分权威、威权家庭、放纵家庭和疏忽家庭方面则不那么重要。因此,在本次调查中使用了接受/参与以及严格程度/监督方面的分数,将家庭划分为以下四类之一。接受/参与量表衡量的是青少年认为他或她的父母有多爱、有求必应和参与(例子项目:“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我可72,M=.81,SD=.11,range=第25至1.0段 评估父母对青少年的监督和监督(例题:“你的父母想知道你晚上去哪儿了多少?”);“我的父母知道我放学后的大多数下午在哪里”;9个项目,a=.76,M=.lA,SD=.13,range=.30到LO)。在这个样本中,维度是适度相关的(r=.34,plt;.001)。对于每个尺度,有几个条目的格式为真/假,而其他的则是在三点尺度上进行比例;在综合指标的接受度和严密性的形成中,项目被加权为^,只是为了缩放方面的差异。Lambom等人(2001年)中给出了每个比例尺项的完整列表。(1991).以指望他们帮助我。”;“当他要我做某事时,他解释为什么”;10个项目,a=72,M=.81,SD=.11,range=第25至1.0段 评估父母对青少年的监督和监督(例题:“你的父母想知道你晚上去哪儿了多少?”);“我的父母知道我放学后的大多数下午在哪里”;9个项目,a=.76,M=.lA,SD=.13,range=.30到LO)。在这个样本中,维度是适度相关的(r=.34,plt;.001)。对于每个尺度,有几个条目的格式为真/假,而其他的则是在三点尺度上进行比例;在综合指标的接受度和严密性的形成中,项目被加权为^,只是为了缩放方面的差异。Lambom等人(2001年)中给出了每个比例尺项的完整列表。(1991).
从历史上看,研究者们在研究家族中的scKiialization时使用了类型学和维度方法。正如我们在别处讨论的(Darlingamp;Steinberg,1993),死两种方法有不同的理论取向,并且基于不同的假设。在类型学传统中,家长的一般模式、组织或氛围是最重要的,对具体的养育方式或层面(如接受或严格程度)的评估是为了启发的目的进行的,以此为了解整个养育环境提供机会。在维度传统中,相反,对亲子关系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评估,以检验他们(分别或共同)与子女调整之间关系的特定假设。每种传统都有其优点,因此,使用其中一种传统的决定应当以法理为依据。
我们决定在本研究中使用一种类型学方法——也就是使用接受度和严格性量表来为类别分配家庭,而不是amp;把这些维度当作连续变量来对待——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个决定反映了我们对研究鲍姆林德(1971)提出,后来由马科比和马丁(1983)提出的具体理论框架的兴趣。摘要鲍姆林德理论是一种关于类型的理论,而不是abcmt具体的父母实践,近30年来对社会化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次,在不同的父母教养环境中,类型学方法更适合于对青少年的短期发展方式进行描述。
通过对被试在接受和严格程度上的三切分,确定了四个父母类型,并同时对女性在Ae两个变量上的得分进行了检验。在Maccoby Mid Martin(1983)之后,权威家庭(JV=817)在接受/参与和严格/监督方面得分较高,而疏忽的家庭(iV=838)在卧铺变量上处于最低。在受累程度上,专制家族(451)处于最低的畸形程度,但在严格程度上是最高的。251例纵情患者受累较多,严格程度最低。在两个维度上处于中间等级的家庭被排除在分析之外,以确保这四个小组的团体代表不同的类别。这个过程是在分析横断面数据(Lamborn等人,1991年)之后进行的,在这里是为了便于比较。用畸形分裂法将家庭划分为亲代组,而不是根据预定的cutoflfe来分配家庭,这就导致了一种典型的家系分类。例如,我们可以信赖的是,在我们的“放纵”类别中,相对于其他家庭而言,我们的“放纵”家庭(即更容易接受,不那么sMct),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试验的“放纵”会是一个“放纵”的群体或历史时期的不同点。在此重要的是,请记住,家庭是一种或另一种相对于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启发性的,而不是诊断的目的因为每年的调查是分成两个部分,在不同的测试日进行,所以有些学生在纵向样本中只完成了一年中的两个部分中的一项。这在综合衡量的评分中偶尔会出现问题,综合衡量采用了这两个调查部分。通常,我们会保守地处理缺失数据的实例,只有在受访者回答了80%的必要项目后才算出复合得分。然而,由于这个过程,我们的Ns在分析中各不相同(倾向于所检查的变量),在任何分析中都不会少于1000个主题。然而由于缺课是数据丢失的重要原因,主要数据分析所针对的样本很有可能在学校的参与程度较高(在其他方面比一般学生更好)。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我们对效果的估计可能过于保守:因为我们的结果度量可能受到了限制,结果和预测值之间观察到的关系被削弱了。
为了使我们更加有信心,这四类家庭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类型(从而加强了研究的内部有效性),该程序从分析中排除了大量以“中等”为父母的家庭(从而削弱了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因此,虽然我们对样本中的极端群体的关注可能提供了对理论的更明确的检验,但我们所选择的方法限制了我们的发现的普遍性。然而,如表1所示,在养育变量上,上、下畸胎的家庭抽样在人口统计学上与整个项目样本具有可比性,表明我们并没有通过使用畸形分裂程序有选择地排除任何人口分组。表2提供了四个父母组的大小以及每个组在接受和严格程度上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的信息。
结果变量。在横断面分析中,四组结果变量被检验:心理社会发展,学术能力,内化困境和问题行为。表3列出了整个抽样结果变量的手段和标准偏差(包括未归为四个养育群体之一的青少年)。表4列出了各项结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平均成绩外,所有结果变量都按4点Likert标度,其中1为低(例如,“从不”、“强烈不同意”、“不喜欢我”),4等(如“频繁”、“非常同意”、“非常像我”)。在平均成绩方面,分数被转换成标准的4.0米,范围从0(全部F)到4.0(都是A)。总之,虽然心理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与学校能力的某些方面存在某些重叠,但表4的模式支持了我们区分四组结果和每组内各种指标之间的区别。在矩阵中,内化痛苦和问题行为的三个测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最高。
心理社会发展的三个指标包括青少年自我感知特征的社会能力分量表(Harter,1982年)和格林伯格的心理成熟量表中的两个子量表——工作定向和自力更生(表格D;格林伯格,约塞尔森,克纳和克纳,1974年)。社交能力量表包括五项,询问学生是否认为自己很受欢迎,有很多朋友,以及容易交朋友。参与者被要求阅读两种选择(例如,“一些青少年觉得他们被社会所接受,而另一些青少年则希望更多的人接受他们”),并选择一个更像自己的人。工作定位(a=73)和自我信任(a=.81),每个分量表包含10个项目。工作定向量表衡量的是青少年成功完成任务的自豪感。反向编码的示例项是“我发现很难坚持做任何需要很长时间的事情。”自我自信量表衡量青少年的内部控制感和自主决策的能力,而不过度依赖他人。反向编码的示例项是“运气决定了我的大部分事情。
衡量学习成绩的三个指标包括总体平均成绩、青少年自我知觉量表的学业能力分量表(Harter,1982)以及为该项目制定的评估青少年入学取向的量表。受访者提供了他们当前平均成绩的信息,分为9个等级,从“主要是a的”到“主要是F”;分数被转换成了标准的4.0等级。自我报告的成绩是很高的与实际成绩从官方学校记录(多诺万和杰索,1985年;Dombusch等人,1987年)。学术能力分量表(a=73)包括五个项目询问学生对他或她的同班同学的智力的看法,迅速完成作业的能力,以及课堂作业的能力。对学校的方向性的测量来自于评估学生对学校的依恋感的一系列项目(Wehl^e,Rutter,Smith,Lesko,amp; Fernandez,1989)。对学校的定位是由六个项目组成的量表。一个样本项目是“我对学校感到满意,因为我学到了很多。”
这三种探测问题行为的方法包括参与吸毒、酗酒、学校行为不端和犯罪的报告。药物和酒精使用的测量利用了吸烟、酒精、大麻和其他毒品的频率(五类,a=.86)。(格林伯格,斯坦伯格amp;沃克斯,1981年)。衡量学校不当行为的标准包括作弊、抄作业和迟到(四项,a=.68)。(Ruggiero,1984)。衡量违法行为的方法包括:携带武器、偷窃和惹上麻烦等行为的发生频率Lice(6项,a=.82)(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英语原文共 22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2087],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