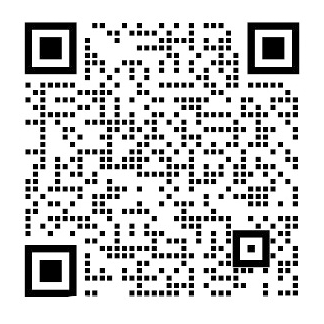Available online at www.sciencedirect.com
Sciencedirect
Lingua172-173(2016)45-61
Coherence in new urban dialects: A case study(excerpts)
ordf;University of Potsdam, Germany
ᵇUniversity of Saarland, Germany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evidence for linguistic coherence in new urban dialects that evolved in multiethnic and multilingual urban neighbourhoods. We propose a view of coherence as an interpretation of empirical observations rather than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out there in the data”, and argue that this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evidence of systematic links between linguistic phenomena, as established by patterns of covariation between phenomena that can be shown to be related at linguistic levels. In a case study, we present results from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es for a set of phenomena that have been described for Kiezdeutsch, a new dialect from multilingual urban Germany. Qualitative analyses point to linguis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phenomena and between pragmatic and linguistic levels. Quantitative analyses, based on corpus data from KiDKo (www.kiezdeutschkorpus.de), point to systematic advantages for the Kiezdeutsch data from a multiethnic and multilingual context provided by the main corpus (KiDKo/Mu), compared to complementary corpus data from a mostly monoethnic and monolingual (German) context (KiDKo/Mo). Taken together, this indicates patterns of covariation that support an interpretation of coherence for this new dialect: our findings point to an interconnected linguistic system, rather than to a mere accumulation of individual features. In addition to this internal coherence, the data also points to external coherence: Kiezdeutsch is not disconnected on the outside either, but fully integrated within the general domain of German, an integration that defies a distinction of “autochthonous” and “allochthonous” German, not only at the level of speakers, but also at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systems.
Keywords
Covariati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herence; Kiezdeutsch; Urban dialects; Bare NPs;Light verbs; Directive particles; German forefield
1. Introduction
Coherence is a concept that is relevant for a lot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mong them philosophy (Lewis, 1946), Bayesian epistemology (Shimony, 1955), quantum physics (Glauber, 1963), epidemiology (Bradford Hill, 1965), higher algebra (MacLane, 1965), and cybernetics (Wolkowski, 2007). What the different notions of coherence in the different fields have in common is reference, in one way or another, to systems and suppor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ir elements. In the sense we are interested in here, coherence is a core property of linguistic system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a domain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n a discussion of coherence is that of multilingual urban contexts. In present-day Europe (as in a number of other regions), these contexts are characterised by a high linguistic diversity – sometimes called lsquo;superdiversityrsquo; (cf. e.g., Vertovec, 2007) – that supports a large range of linguistic repertoires and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language contact. Among others, this has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variants of the respective majority languages that reflect the special dynamics of this diverse setting.1 For a discussion of coherence, these new variants ar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because their status as proper, identifiable systems is still controversial, not only in linguistics, but also in public discussion, where they are subject to intense, sometimes heated discussions.
In linguistics, the controversy focuses on such questions as whether these new variants represent full-blown linguistic systems in their own right, whether they can be described as dialects or varieties, and whether they are spoken consistently (cf. e.g., Auer, 2013 for a discussion of Kiezdeutsch in Germany, lit. lsquo;(neighbour-)hood Germanrsquo;, a German example for such a new way of speaking in multilingual urban neighbourhoods). In contrast to this, public discussion approaches the status of such variants from a quite different angle. Here, the issue is predominantly framed within a language ideology that excludes them from the domain of “proper”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新城市方言的一致性:案例研究(节选)
波茨坦大学
德国萨尔州大学
摘要:本文研究了在多民族和多语种城市社区中发展的新城市方言中语言一致性的证据。我们提出一个连贯性的观点,作为对实证观察的解释,而不是“数据中的”的一些解释,并认为这种解释应该基于语言现象之间的系统联系的证据,可以表现出与语言层面相关的现象。在一个案例研究中,我们从定性和定量分析中提出了一系列现象的结果,这些现象已经被描述为Kiezdeutsch,一种来自德国多语种城市的新方言。定性分析指出了不同现象之间的语言关系,以及语用水平与语言水平之间的关系。基于KiDKo(www.kiezdeutschkorpus.de)的语料库数据的定量分析指出,由主要语料库(KiDKo / Mu)提供的多语言和多语言环境中的Kiezdeutsch数据的系统优势与主要的辅助语料库数据相比之下,大部分是单民族和单语(德语)上下文(KiDKo / Mo)的补充语料库数据。相比之下,大部分是单民族和单语(德语)上下文(KiDKo / Mo)的补充语料库数据。我们的发现指向一个相互关联的语言系统,而不是仅仅是个体特征的积累。除了内部的一致性外,数据还指出了外部的一致性:Kiezdeutsch在外部也没有断开连接,而是完全融入了德国的一般领域,这种一体化不符合“本土化”和“同性恋”德国人的区别,不仅在发言人层面,而且在语言系统层面。
关键词:共变 内部和外部的一致性 Kiezdeutsch 城市方言 裸露的NPs 光动词 指示粒子
- 引言
连贯性是一个与许多不同学科相关的概念,其中包括哲学(Lewis,1946),贝叶斯认识论(Shimony,1955),量子物理学(Glauber,1963),流行病学(Bradford Hill,1965),高代数MacLane,1965)和控制论(Wolkowski,2007)。不同领域的一致性的不同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某种方式参考其要素之间的系统和支持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这里感兴趣,一致性是语言系统的核心属性。
在这种背景下,在一致性讨论中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是多语言城市环境。在当今的欧洲(如其他一些地区),这些背景的特点是高语言多样性 - 有时被称为“超级多样性”(参见,例如,Vertovec,2007) - 支持大范围的语言曲目和丰富语言接触的机会。除此之外,这导致出现了反映这种多样化环境的特殊动态的各种多数语言的新变体.一个是对于一致性的讨论,这些新变体特别有趣,因为它们作为适当的可识别系统的状态仍然是有争议的,不仅在语言学上,而且在公共讨论中,他们受到激烈的,有时热烈的讨论。
在语言学中,这个争论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这些新的变体是否代表完整的语言系统,无论它们是否被描述为方言或变体,以及它们是否被一致地说出来(参见,例如,Auer,2013年在德国为Kiezdeutsch所做的讨论,lit(neighbour-)hood德语,一个德国例子,一种新的多语言城市社区的方式)。与此相反,公众讨论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处理这些变体的状态。在这里,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一种语言意识形态中,将它们从“正确的”或“正确的语言”领域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否认他们有系统的多样性或方言的地位,是将其贬值为“错误的”言论而不是一种合法的语言变体,从而最终支持发言人的贬值和其他方式(参见Wiese,2015 年为这些模式所做的更详细的分析)。因此,语言系统性的证据和一致性的解释不仅从语言学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且对于公共传播也是有意义的,在公共传播中,它们可以有助于抵消通过语言代理发挥的社会排斥倾向。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语言一致性概念(第2部分),然后提出一个充分阐述我们的概念建议的案例研究。
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进一步发展我们的语言一致性概念(第2部分),然后提出一个充分阐述我们的概念建议的案例研究。我们的案例研究的主题将是Kiezdeutsch的数据。我们将首先描述为我们的研究提供经验基础的语料库数据,KiezDeutsch Korpus(第3部分),然后使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来研究该数据的语言一致性问题(第4部分)。最后一节将我们的结果汇集在一起,并讨论这些发现对于语言变化和变化背景下对新语言模式的理解的影响(第5部分)。
2.一致性作为数据的解释
对这一卷的贡献之间共同的一般观点是作为不同语言变量之间关系的一致性。鉴于这个基本假设,这种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它在什么级别上呢?与这个卷中的其他两个概念如何相配合:共变和混合?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些关键问题,为我们在基茨德省的案例研究中建立概念基础。对语言现象(品种,风格,发言方式)的一致性的任何实证调查的关键点是承认一致性不是我们在世界上可以观察到的东西,而是对我们的观察的解释,我们的做法意义上的数据。这与所指出的类似,例如,因果关系,一些学科与一致性紧密相关的概念2:当我们对广泛的社会,心理和身体领域进行因果推理时,习惯性地归因于因果关系与现象的关系,因果关系本身并不是经验可访问的东西,而是我们为观察到的共同事件而开发的一种解释。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A导致B,而只有A和B才会一起发生 - 或者,如休谟(1740)把它用在讨论因果关系中,A和B是“不断联结”的。同样,我们不能直接观察到语言现象P是一致的,而只是将其作为对我们对于P的经验和理论发现的解释。然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致性调查并不一定与社会语言学方法如Ramptonetal冲突。他陈述了“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出现,对代理,分裂和意外事件兴趣的兴起削弱了语言学家传统上的假设,系统和一致性在他们的数据中,等待被发现”(Rampton等,2014:5)
“数据中的”是什么是现象的共同发生,更具体地说,共同出现和语言模式的可能变化,这是本卷标题中所提及的第二个概念,“共处”。 “数据中的”是什么是现象的共同发生,更具体地说,共同出现和语言模式的可能变化,这是本卷标题中所提及的第二个概念,“共处”。然而,如果我们想调查一致性,我们不只是寻找或多或少的随机元素A和B的协变量,而是寻找相关变量的协方差。为了使我们将这些模式解释为一致性,这些关系的性质应该使得A和B具有共同点,例如它们分享特定要素或基于重叠的来源。这种共同点以及所观察到的协方差可能表明,A影响B,A是B出现的驱动力,B取决于A,反之亦然,或者受到相同来源的影响。重要的是,A和B以一种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说是有意义的方式相互联系,提出了一种系统,而不是孤立的个体因素。可能的模式可能是例如其中一些元件是连接几个其他元件的焦点,而其他元件具有更多的外围位置。对于一致性的解释,我们不需要对链接的具体模式做出任何假设:关键是网络的存在。那么,这个一致性比一个来自控制论的显着的一个弱点(参见Wolkowski,2007),其中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同态性是一致性的先决条件。图。 1给出了我们在这里建议的一致性视图的图示一致性作为互联关系的一种模式。
图1
一致性作为互联关系的一种模式。
这种一致性观点有两个重要方面:(1)如上所述,一致性的特征是对数据的一种特殊解释,但至关重要的是基于语言分析,而(2)这种分析最初是针对语言系统的水平。 3第二部分涉及Rampton等人提出的一个中心点。引用上述,也是本卷题目中提出的最后一个术语,即“bricolage”。如果我们从语言系统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数据,我们可能会发现支持解释一致性的证据,如果我们看待发言人的实际语言行为以及他们在不同语言情境下做出的不同选择,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显然,作为其语言行为的代理人,演讲者不仅仅是从一个来源使用语言元素,而是在任何给定的交际环境中选择更大的游戏池。特别是在当今城市欧洲发现的高度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背景下,演讲者的曲目可以包含来自各种不同代码的元素,不仅包括不同的风格和寄存器,还包括不同的方言和语言。他们可以以多种创造性的方式利用这些资源,导致出现了遗产和多数语言的新的发言方式,以及违反固定的“语言 - 体位”关系的代码转换,混合和交叉的模式(参见Quist,2010)。
这种高度的语言多样性及其固有的动力学引起了我们是否在这里处理不同的品种,或者说是流行的风格或风格的做法的争议.4然而,虽然我们同意发言者的语言行为太多异,支持代表其所有曲目的单一,独特的品种,这并不意味着在语言层面上没有任何形成其资源一部分的可识别语言系统。正是这些制度,我们认为我们对一致性的解释应该是:讲话者可以从不同的资源中自由选择,混合,合并,并结合他们的交际行为,支持不同的社会认同行为,语言元素本身将彼此互动,依赖彼此,并在不同的语言模式之间相互影响,从而在语言层面形成自己的可识别系统。图2说明了这一点,根据语音情况,可以访问和组合的演讲者可以从不同的,可能重叠的语言系统的各种各样的语言层面的元素到语言层面来解读一致性。
图2
演讲者资源的多样性与语言系统层面的一致性。
当寻找这样的系统时,我们应该将语言数据(这种数据不是从特定语言或品种的先入为主的概念,而是从典型的语言情境的角度来定位)集中起来,从而识别特定语言元素的相互作用领域。那么,在这种传统传统中的“理想的发言者”和“现代的演讲者”的概念中,超越了老式的辩证法和社会语言学方法(参见Eckert,2003年的批评):我们不是在看对于一直使用特定语言代码的发言者,在一定程度上和/或总是使用语言系统,可能会出现在某些语言情境中发现的交际行为中经常使用的语言系统。
为了支持“一致性”的解释,那么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语言数据中寻找模式,提出不同现象之间和/或不同语言层面之间的系统联系,我们应该看这种模式的特定语言情境。
我们的案例研究的相关言论情况是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青少年混合群体(包括大多数语言的单语者,在这种情况下是德语)的非正式同伴群体对话,已被证明是一种支持我们感兴趣去用的说话的新方式。
5.一致性,语言变异与变化:新城市方言的生态学
在本文中,我们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在语言一致性调查中。作为我们的起点,我们提出了一致性观点,作为对实证观察的解释,而不是“数据中的”的一些事物。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应该基于语言现象之间的系统联系的证据,这是由语言层面上可以显示相关的现象之间的协变模式所确立的。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认为,在过去几十年来,在多民族和多语言的欧洲出现的新的城市方言的一致性调查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领域。这些方言出现在高度多样化的环境中,其特征在于大范围的接触情况,多样化的曲目,以及语言变异和变化带来的快速步调,从而为连贯性假设提供了有趣的挑战。
我们认为,在这里支持新品种的内部一致性并不能使得基德德与“本土德国人”不同,而是以这种方式成为一种异化因素。相反,如果仔细观察数据,通常会发现,Kiezdeutsch的特征指出了德国其他品种中也能看到的持续变化,尽管有关现象可能还没有开发出来(或者说至今没有开发出来),也就是说,它们可能不像Kiezdeutsch那样普遍、频繁、系统化。
确定因子缩小的案例,确实反映了现代德语的一般趋势,从语音减少和强制化到完全省略.18从前面的部分可以看出,我们调查了KiDKo / Mu的Kiezdeutsch现象,在每种情况下,还使用更多单语言语言社区的数据证实了补语语料库KiDKo / Mo,表明相对而不是绝对差异。 Kiezdeutsch的特征对德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也不一定是小说。从Kiezdeutsch(以及在Auer,2013年)经常提到的分析中,我们分析了两个例子:至少在公共交通站点的裸露地方NPs已经是近一个世纪以前的纯粹主义语言沮丧的话题了 - 而且可能早一点,参考(14)。早在15世纪,我们发现与我们为Kiezdeutsch(参见(15))描述的V3模式非常相似的句子,19表明,新高德的V2可能不是通常假设不灵活,但是较早前更广泛使用的字词选项可能仍然以非正式口语语言保持20:
(14)“今天,我们几乎要说:只要可能,介词都将被省略,无论我们看出什么样的关系,都不会被表达出来。这意味着除了:我们,就是我们的语言变得沉默了。在火车站一听到:火车去V柏林?不,火车去汉堡;在电车上:我要去V墓园。“(Briegleb,1932:16)
表选项
(15)达累斯萨拉姆NACH死埃德尔kungin附耳enhalb奥芬奥夫DES Laslaes广域网gueter ...
后有高贵的女王从奥芬就在Laslaes广域网屋
“之后,高贵的女王从奥芬去了拉斯劳斯的庄园......”
表选项
这表明,Kiezdeutsch在支持内部一致性的解释的同时,也没有在外部断开连接,而是完全融入了德国的一般领域:是一个与德语的其他变体的整合,这个整合不仅在讲话者层面,而且在语言系统层面区别了“本土的”和“外来的”德语。这就是为我们提供了针对现代德语中语言变体和变化研究的优势,与“相对静态的传统方言”相比,它是一种动态的“全面发展”中的新方言(Hinskens,2011)。正是这些动态使得Kiezdeutsch成为一个特别有趣的研究对象,而我们发现内部和外部一致性的证据表明,Kiezdeutsch提供的证据与这个年轻的方言本身相关。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29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