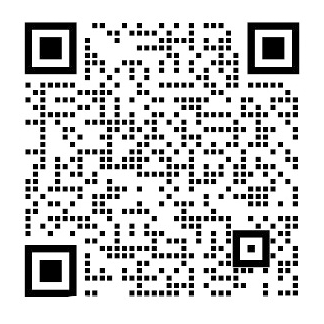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
作者:Judith May 单位: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矛盾的地形
玛丽·卡迪纳尔1975年自传体小说的女叙述者,《说出来的话》(Les Mots pour le dire)一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与过去十年中定义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的问题极为相似。小说讲述了作者和叙述者在精神分析方面的经历,以及她与一位精神病学家的相遇。卡迪纳尔的“治愈”标志着她越来越有能力讲述自己的过去,从而为自己的梦想、幻想和恐惧创造新的隐喻和形象。到小说结束时,她自己也成了作家。
在叙述者反复出现的幻觉中,她被一只用金属管固定在右眼上的眼睛所观察和恐吓。一个复杂的联想网络揭示了这幅图像的来源。小时候,她和父亲、保姆一起在树林里散步,她有小便的冲动,保姆把她带到一棵树后面。突然,女孩听到一声响亮的呼噜呼噜声。她转过身,看见父亲站在她身后:“他的一只眼睛前面拿着一个有趣的黑色东西,是一种金属动物,管子末端有一只眼睛。那就是制造噪音的东西!我不想让他看见我。”
这一场景唤起了电影在父权至上的时代的力量,一个女儿的隐私——实际上是她的身体——被她的父亲用电影摄像机拍摄所侵犯。这个场景暗示了表情的力量:男人是“表情的承载者”,女人是表情的对象。这是劳拉bull;马尔维在她1975年的文章《视觉愉悦与叙事电影》中用来描述传统电影中外观的功能的词语,它们也许是最简洁地概括了女权主义电影批评的范围。“在一个由性别失衡所决定的世界里,欣赏的乐趣被分为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马尔维写道。“决定性的男性凝视将它的幻想投射到女性身上,并相应地赋予其风格。在她们传统的暴露角色中,女性同时被注视和展示,她们的外表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和情色影响,因此她们可以被说成是被注视。”
电影也结合了叙事和景观,即讲述和展示的功能,它是由视觉的性别层次构成的。这里也存在性别失衡,主角或叙述者的男性角色补充了男性外表的权威。这种叙事与奇观之间的关系也指出了女权主义电影理论与《说出来的话》中所涉及的问题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上述时刻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与以男性为中心的奇观之间的对抗。这部小说的叙述包含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记忆过程,一个女人与过去、与家庭的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在回忆这一特殊的事件时,这个女人重新创造了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父亲可怕的凝视被冻结了很多年;因为她童年时代对她父亲的不检点所产生的愤怒,在当时的幻觉中已经被压抑下去了。换句话说,这种叙事和景观的相遇,让男性的目光失去了力量。女权主义影评人可能并不都是被这样一个创伤性的场景所激发,但卡迪纳尔用电影摄像机唤起了对爸爸的回忆,这是女权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的恰当隐喻,通过这种叙事,电影奇观被记住并重新定义。
最近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说出来的话》一书,以及它在精神分析、女性身份问题和女性写作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是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核心。劳拉bull;马尔维假设精神分析是女性主义和电影的一种特殊的研究模式,这种假设是基于电影本质上是精神分析的灵魂伴侣这一假设之上的。女性主义影评人被女性写作和身体理论所吸引,尤其是那些与法国女权主义者有关的理论,如海伦·西克斯、卢斯·伊瑞加雷和茱莉亚·克里丝特瓦。红衣主教的小说中,女权主义问题相关联,通过法国先锋派写作和一个激进的使用精神分析想起好莱坞版的精神分析,即一个创伤事件的回忆提示必要的幸福结局,通常暗示结婚誓言。书中所揭示的秘密和过去的事件可能不会导致一对幸福的夫妻(或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走向夕阳的好莱坞式的结局,但它们却让一个胜利的结论成为可能:一个曾经支离破碎的个体现在在她对自己的认识中得到了统一和安全。在她们最近的作品中,女性主义影评人所接受的精神分析观点挑战了整个主题的概念。然而,好莱坞电影对统一自我的虚构保持了其独特的吸引力。因此,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的项目正是通过叙述者在《说出来的话》中的旅程恰当地呈现出来的,因为它处于好莱坞和潜意识之间的矛盾地带,处于男权过去的形象和女性现在的结构之间。
如果说过去十年大多数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都是对劳拉bull;马尔维文章中提出的问题的含蓄或明确的回应,这只是稍微有点夸张。这些问题包括:电影作为景观和叙事的中心,精神分析作为批评工具。我调查这部作品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女性主义和电影的“矛盾地带”。我认为,关于女性和电影最有趣、最具挑战性的作品——最有趣的是它要求我们思考电影、思考文化内部和文化内部的形象,最具挑战性的是它给女权主义作品整体带来的独特视角——解决了矛盾的核心问题。以电影为例,这意味着对好莱坞电影的迷恋和蔑视同时存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意味着对父权制压迫和脆弱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种感觉,即女性主义的工作就是利用这种脆弱,同时充分了解强烈反弹的危险。
美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的发展受到三股主要力量的影响,这三股力量和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本身一样,都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现象:妇女运动、独立电影制作和学术电影研究。虽然前两个运动强调女权主义影评人的政治议程,但大学电影研究强调的是理论——不一定是非政治的,但肯定不是政治的。
从一开始,当代美国妇女运动就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焦点。女权主义者对男权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女性的刻板印象的关注,使电影——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好莱坞——成为了批评的对象。女权主义电影批评的第一阶段主要关注女性的电影形象以及她们与女性现实生活的差异。由于许多被吸引到电影研究的女性是在视觉文化中长大的第一代美国人,她们同时认识到图像的力量和其中呈现的女性特征的力量,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玛乔丽·罗森在《爆米花的维纳斯》的序言中提出的问题,传达了这一发现的巨大意义:“好莱坞的价值观对像我这样容易上当受骗的公众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公众,尤其是女性,会如此被动地接受这个行业对生活的诠释呢?
受到独立电影制作和妇女运动启发的新女权主义纪录片也旨在摒弃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茱莉亚·赖克特和詹姆斯·克莱因的《成长中的女性》(1971)和盖里·阿舒尔的《简妮的简妮》(1971)等电影以一种直接的、可理解的方式提出了女权主义问题,作为一种提高政治意识的形式。虽然女性独立电影并不局限于纪录片,但女性独立电影对女性问题的明确关注,使其成为独立电影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最具决定性的影响。
妇女运动和独立电影制作似乎为女权主义电影批评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议程:揭开好莱坞“负面”形象的神秘面纱,赞扬女权主义电影制片人提供的“正面”形象。但同样受到电影研究新发展的影响,女权主义者开始质疑女性作为“形象”的概念。
与此同时,文学符号学家们也在用非语言形式,如电影,来测试语言范式,这使得学术界对电影研究的兴趣重新燃起;“跨学科”研究在大学内部同时变得越来越重要。电影研究的理论范围是严谨而复杂的,特别是英国杂志《银幕》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银幕是塑造当代电影理论的方法论最重要的试验场: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每个问题的核心是代表性问题。根据符号学家的观点,电影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二元对立的系统网络,即使不是字面上的,也是隐喻性的,就像语言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受路易斯·阿尔都塞影响的人,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表现的功能,而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媒介的功能将通过它对观众的称呼形式来评估。精神分析评论家,尤其是那些追随雅克·拉康的评论家,坚持认为,在电影识别中,视觉,以及由此而来的观点结构,是核心,在这里被理解为主体的一种想象的一致性。如果说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是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产生的,那么它似乎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套用一句古老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女权主义似乎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解电影的方式,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改变电影的方式。
马尔维从一个理论家和一个电影制作人的角度审视了经典的叙事电影,也就是说,现实主义电影使用了十九世纪小说的基本叙事手段:危机和解决的情节,读者/观众和角色之间的强烈认同,以及一个整体的视角,或者说叙事智慧。当然,“古典叙事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几乎可以互换使用,这是好莱坞在美学和文化意义上定义电影的中心作用。于是,马尔维提出了一种对经典叙事电影的去神秘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另类的电影实践的可能性。虽然马尔维的结论是,女性主义电影的目标是摧毁与古典电影相关的娱乐形式,但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好莱坞的吸引力比她预期的要强烈得多,玛维本人也重新评估了这一立场。约翰斯顿认为,不应如此迅速地宣称古典电影是女权主义目标的敌人:“在这个时候,应该制定一项战略,既将电影视为政治工具,又将电影视为娱乐。长久以来,这两个对立的极端几乎没有共同点。”
尽管女权主义者在古典电影理论和女性电影评价之间建立了联系,但我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女权主义在电影上的一贯表现。所有女权主义批评家的主要任务是重新思考二元论本身,这个过程被E. Ann Kaplan描述为需要超越那些“长期存在的文化和语言对立模式”。然而,最令人兴奋的女性和电影作品的核心是矛盾:无论人们多么渴望“超越自我”,这种二元论模式都有一种催眠的力量让人着迷,尤其是投射在电影屏幕上的时候。
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电影
我曾提出,矛盾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的中心问题,对许多观察家来说,精神分析在最近众多女性主义电影作品中的中心地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在当代电影理论中,19世纪末电影和精神分析的同时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被用多种方式描述过,从电影对精神分析理论中恋母情结危机的强迫性再现,到作为弗洛伊德对精神装置描述的表现形式的电影。即使是电影最基本的特征也暗示着相似性——从投影和识别到做梦和看电影之间的相似性。
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中,精神分析之所以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主题,与其说是它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维度,不如说是当代的观看主体理论以雅克bull;拉康的作品为出发点。“镜子舞台”与电影银幕之间有着几乎不可抗拒的契合,想象与象征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电影观影的一个宏大隐喻,同时也是一种倒退与专制。对于电影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来说,性别差异是中心的,决定性的力量。
很明显,拉康关于性别差异的观点和女权主义的观点并不必然相交,拉康具有性别歧视特征的智慧使许多观察家很难理解他的作品对女权主义者可能有什么兴趣。对精神分析的批评挪用当然是可能的,当然,危险在于“挪用”和“合作”之间的细微差别。正如莱斯利·斯特恩所写的那样,“虽然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们不会否认电影话语中对父权无意识的描述,但这样的断言存在一种危险,即它在展示压迫和诱惑的二元性时就停止了,并阻碍了女性欲望的问题:谁在说它,它是如何说的?”很多时候,“女人的欲望问题”仅仅是在精神分析的范围内提出的,它把女人排除在象征之外。正如斯蒂芬·希思所说:“颠倒的差别也是维持着的差别。”这个问题已经被各种理论家所讨论,他们将精神分析置于女权主义的框架中;卡娅·西尔弗曼对符号学中的主体理论和符号学中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特别清晰的阐述。
在电影中,精神分析与女权主义的交集,以及其他方面,都被激烈地争论着是支持还是反对精神分析。在我看来,更关键的问题是,精神分析是否构成了一种理论,让女权主义者有了新的视角?或者,有没有一种女性主义的电影理论,可以从其他话语中借用,但它本身仍然构成了一种理论?这些关于女性主义作为电影理论的地位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被提出。
如果二元论和性别差异是精神分析中的强迫性关注点,就像在电影中一样,那么女权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在坚持其他方法的可能性的同时,参与二元论。特蕾莎·德劳瑞蒂斯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女权主义、符号学、电影。除了符号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形成理论外,德劳瑞蒂斯还坚持认为,女性作为形象(男性主体的客体)和女性作为历史定义的主体之间的独特而不可缩小的差距,在对差异和表征的分析中往往被忽视或压制。在德劳瑞蒂斯看来,女权主义理论的目标不是对这种差距进行某种乌托邦式的调解,而是以女性作为历史主体的名义,清晰地表达其所伴随的矛盾。
女性电影和女权主义批评
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女性主义影评人已经习惯于不仅问如何定义女性电影,而且问它是否可以被定义。从最好的方面来说,这意味着女性电影的定义在理论上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其中关于女性和/或女性电影的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在肯定女性对电影的贡献方面存在一定的犹豫。女性替代古典电影的定义并不总是清晰的:女性电影人应该以某种方式“解决”好莱坞电影的矛盾吗?或者,他们对其矛盾的分析是否应该导致一种新的电影实践和理论,以一种批判和自我反身的方式审视电影语言的结构?如果前一个目标天真地认为审美干预可以发生在一个不矛盾的领域,那么后一个目标就有可能将女性电影限制在影评人理论关注的一面镜子上。
对女性电影的定义既包括对过去女性参与电影制作的探索,也包括对近期女性电影制作的研究。第一种可能涉及重读电影历史,找出鲜为人知的女性导演,或者评估女性在电影行业工作的“隐藏”方式:担任剪辑和编辑,担任编剧,担任可能在电影中行使了一些艺术控制权的女演员。然而,总的来说,女性主义对电影史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电影导演身上。
多萝西·阿兹纳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唯一一位在好莱坞获得成功的女性导演之一,她的成功成为女权主义电影评论家们的一个重大发现。阿兹纳的电影并不一定被视为女权主义电影,而是从内部批评好莱坞电影惯例的电影。克莱尔·约翰斯顿写道,“总的来说,阿兹纳电影中的女性通过越界和欲望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寻找一种超越男性话语之外的独立存在。”约翰斯顿对阿兹纳作品的评价是建立在批判的局限性基础上的,由此提出的关键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将现存的话语形式一扫而空,以建立一种新的语言形式”。
尽管约翰斯顿一直主张与好莱坞电影进行批判性接触的必要性,但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英语原文共 21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4421],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课题毕业论文、文献综述、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