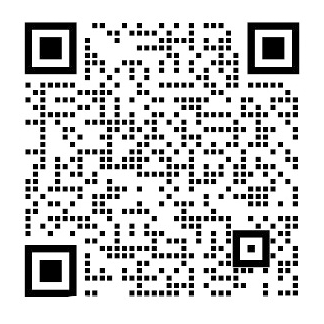Liuse von Flotow.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Manchester: St. Jorome. Publishing, 1997
Page35-45
3. Revising Theories and Myths
Feminist influence o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s most readily visible in the meta texts - the statements, theoretical writings, prefaces and footnotes that have been added to work published since the late 1970s. In these texts a noticeable trend is the developing sense of self exhibited by translators, increasingly aware that their identities as gendered rewriters enter into their work. Translators are introduc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ir work, and offering explanations for it. They are exerting further influence by writing scholarly essays and workshop reports that draw attention to the work of translators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and biographical research that often accompanies a translated text. Other theoretical work is visible in criticisms of the conventional rhetoric of translation and the myths surrounding it. This is all part of a concerted move away from the classical invisible translator, the idea of the translator as some kind of transparent channel whose involvement does not affect the source or the translated texts. With gender viewed as an integral factor in textual production, attention ha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politically aware and sometimes politically engaged translators, who are conscious of their influence on the text and may seek to impose it overtly. However, it is often considerably easier for a translator to proclaim political action in prefaces and other materials than to actually
take a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this may explain the manifesto-like quality of the more combative statements, a quality that is not always reflected in the translated work. This chapter will discuss the mor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that result from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translation,
noting the tentative and ethically difficult processes by which women translators have extricated themselves from the classical notion of submission to the original.
Proliferating Prefaces: The Translators Sense of Self
Translations published in a cultural context affected by feminism are remarkable for the metatexts that draw attention to the translator-effect, the mark each translator, as a gendered individual, leaves on the work. In the case of translators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feminists, these
texts display a powerful sense of the translators identity. As Jean Delisle has shown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astonish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medieval translators and feminist translators, the feminist translating subject 'is explicitly present, affirming feminine and feminist values'
(1993:209; my translation). In Canada, the feminist translators sense of self is reinforced by other paratextual items such as translator/author photographs and translator/author bio-bibliographies, which in no way make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uthors and translators respective contributions or positions.
The Canadian scenario may be something of an anomaly, specific to a situation where related feminist interests have come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in a fortuitous mix. Delisles assertion that the translator sees herself as co-author of the new (translated) work (1993:223) may not
apply in all cases. The more conventional view that still pertains in many cultures has recently been described by German translator Beate Thill (1995). In a study of the prize acceptance speeches made by women translators and published in Der Ubersetzer, the German translators journal, Thill found that these women translators described their work
in the most humble terms: they are the sherpa silently bearing the burden and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master; they are ferrymen (sic), transporting materials and running errands between cultures; their work is one of transition, and thus transitory. In Thills assessment, this modesty, maintained despite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and public recognition, is linked to problems of identity. Translators live between two cultures, and women translators live between at least three, patriarchy (public life) being the omnipresent third. Womens socialization into the private sphere, where empathy, submissiveness and industry are valued, and the double orientation they must undertake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 professional life may render them uncertain, oscillating, continually having to cope with an ambivalence of identity. This partially underlies their self-evaluations as sherpas or coolies of the literary market. Such rhetoric is what contemporary English-language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eek to overcome, as they incorporate the subjective and gendered aspects of the translator-effect.
Asserting the Translator s Identity
Suzanne Jill Levine goes to some lengths to explain the attraction the Cuban writers had for her despite their misogynist thrust; and her explanations clearly involve her personal identity and interests: she responds to the punning, streetwise language of Cabrera Infante because of her own New York Jewish sense of humour. She assumes the licence to subvert aspects of Cabreras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writers work, because she has discovered the grounds for such subversion in their work. The authors own view that translation is 'a more advanced stage of writing' (1983/1992:79) makes it easier for her to impose or extend wordgames or alliterations in English, since she is thereby advancing their writing. The authors literary styles favour subversive multiplicity and openness leading her to draw parallels to feminist views of women as a subversive element. In other words, her subjective readings of
these works are the basis for her equ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
利乌斯·冯·弗洛托
第35-45页
- 修正理论和神话
女性主义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影响,在元文本中最常见,例如一些声明、理论著作还有自1970年代末被添加到作品中的序言和脚注。在这些文本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译者表现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译者意识到性别色彩会影响他们的译作。他们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介绍和评论,并解答疑问。他们通过撰写学术论文和“工作报告”进行与文学和传记有关的翻译研究,对译者的工作和历史进行了进一步的影响。此外,对传统的翻译修辞及神话的批判也体现出一些其他的理论。这一切都来自于经典的“隐形”翻译家,译者是某种透明的介质,他们的参与不影响原文与译文。随着性别被视为语篇制作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越来越关注政治意识,有时参与政治的译者,意识到他们对文本的影响,甚至会有意的利用这种手段达到目的。对于译者来说,在序言和其他内容中宣布政治主张往往要比在翻译中容易得多。这也可以更好的解释为什么一些好战性的宣言有时不会在译作中被真实的反映。本章将讨论性别与翻译交集所产生的理论发展,注意到女翻译家从古典观念中解脱出来的尝试和困难过程。
增加序文:译者的自我意识
受女权主义影响的文化背景下出版的译作,以带有“翻译家效应”的文章为代表。每一个译者,作为一个有性别差异的个体,都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痕迹。以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翻译者为例,这些文本对译者的身份认同有很强的感知力。正如让·戴利索在讨论中世纪翻译家和女性主义翻译家的相似之处时所展示的那样,“女性主义翻译主体”明显肯定女性和女权主义价值观。(1993:209)。在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家的自我意识被翻译、作者照片、翻译家和书目等其他因素所强化,这对作者和译者各自的贡献和立场没有任何影响。
加拿大可能是一个特例,特别是在相关的女权主义利益聚集在一起这样一种情况下。德莱斯利声称译者认为自己是新作品的合著者(1993:223),这一断言也许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况。德国翻译家贝特·希尔(1995)最近描述了在许多文化中仍然存在的更为传统的观点。在一篇关于女性译者获奖演讲的研究中,德国德语翻译杂志《Thill》杂志发现,这些女性译者描述的作品,用最卑微的话说:他们是默默承受重担的“夏尔巴人”,跟随着主人的脚步;他们是“渡船人”(原文),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运输物资的跑腿人。他们的工作是过渡的,因此是短暂的。希尔的评论令人印象深刻并取得了公众的认可,这与他的身份和谦逊有关。译者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女性译者至少生活在三种文化之间,父权制(公共生活)是无所不在的第三种文化。妇女的社会化进入私人领域,那里重视执着、顺从和勤劳,而她们参与职业生活时必须采取的双向适应可能会使他们不确定,摇摆不定,不得不时时应付“身份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他们的自我评价,即“夏尔巴人”和“文学市场的苦力”。这样的修辞是当代英语语言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因为他们包含了“译者效应”的主观性和性别两个方面。
译者的身份
苏珊娜·吉尔·莱文(Suzanne Jill Levine)竭力说明她对古巴作家们的兴趣,尽管他们有歧视女性的倾向,但是她的解释显然涉及到她的个人身份和兴趣:由于自己带有纽约犹太人的幽默感,她对卡夫雷拉·因凡特的双关语和街头语言做出了回应。她获得了“颠覆”卡布雷拉和其他拉丁美洲作家作品的许可,因为她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可以“颠覆”的理由。作者自己认为翻译是“更高级的写作阶段”(1983/1992:79),这使她在英语中更容易使用文字游戏和同义词。作者的文学风格倾向于颠覆性、多样性和开放性,她把女性主义的女性观点比作是一种“颠覆性”因素。换句话说,她对这些作品的主观看法是她翻译的基础。莱文在“翻译的效果”中明确包含了个人传记信息,并借鉴了当代权威女权主义理论家,如多姆娜·斯坦顿、朱莉娅·克里斯代娃和海琳·西克斯的观点。为这些妇女的工作合法化提供了理论支持,她认为这是重要的。这些权威的参考起源于早期致力于翻译工作的女权主义者。但这也是因为,“在一个女权主义的时代”,她需要证明翻译(合著)材料不一定支持或支持女权主义思想。
卡罗尔·迈尔翻译奥克塔维奥·阿尔芒的思想来源于类似的方法:她的《美国女权主义背景》与一篇抨击女性主义的古巴文章相冲突(迈尔,1985)。她的随笔用第一人称,记录了她对阿尔芒的男子气概的看法,并试图调和女权主义伦理观与父系社会的矛盾。就像莱文一样,译者的声音和女权主义者的良知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心声。
她的翻译在多大程度上反应了个人因素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女性译者多次提到关于她自己、她的性别还有文化背景对她译作产生影响的部分。这与加拿大最多产的女翻译家希拉·费奇曼最近在一个评论员对她的工作提出问题时重申的“夏尔巴”和“苦力”隐喻中表达的传统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说,我很开心,至少他们知道是译者创造出英文译本,我们要求的并不多。费奇曼无疑是一个较老的翻译家,他们把他的作品看作是无形的。女权主义翻译家和激进女性主义者拒绝这一立场。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得到承认,译者的个性得到承认,并愿意将自己的工作纳入“责任和责任之光”(Kolias 1990:217)。因此,大量引用了传记、政治派别、性取向和民族背景的前言、介绍和评论了译者(戈达尔1986:7)。最近,艾丽斯·帕克(1993)尝试将性实践与发展“多性别”或“多性”翻译理论联系起来;德洛比尼埃-哈伍德(1995)展示了个人发展与她作为译者身份的密切联系。马拉特(1989)使她与lsquo;激进的女同性恋rsquo;思想的政治关联成为她与布罗萨德合作翻译的基础;弗洛托(1995)讨论了译者个人传记在文本选择和翻译中的作用。在北美学术期刊如现代语言协会出版物(1996年10月)的讨论中表明,个人总是会影响文本的制作、翻译和学术工作。目前,这些也是学术反思的素材。当这些方面在翻译中显现出来时,它们就破坏了对翻译的“无形”和对文本的“客观”解读。
对“意义”负有责任
女性译者不仅把自己的个人发展和政治立场引入到翻译中,更有意识地将译者的主观意识纳入到工作中来。他们同时承担着学者和教师的角色,这一角色在论文中最为明显,评论往往是伴随着作品的翻译而“被遗忘”或散布在选集中。译者在这类文学实验中扮演着翻译、教育者和专家的角色。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芭芭拉·戈达尔关于魁北克女权主义作家尼科尔·布罗萨德和法国理论的著作。她解释了一些无法翻译的文字游戏,比如法语中不发音的“e”。她接着解释了这些特征的意图:她说,e是作者用来表示在那里进行的活动中没有女性,删除这个用法“强调了从女性沉默走向中性语法的过程”(戈达尔1983:7)。然后,她指出了用来补充她的英文版本的方法:图形模式和文字游戏,比如他的故事和她的故事,这些都是英语女权主义者比较熟悉的。在一次教育活动中,她最后提请人们注意非学术性英语读者可能会忽略的文本的其他方面,并注意到当代法国理论家德里达和德勒兹的引用文献,所有这些都写在一页纸上。
在随后翻译的洛弗尔(1986),图论(199a)和有形词(1991 B)中,序言的篇幅越来越大。在“洛夫舍尔”一书中,戈达尔首先提到了译者的序言,作为译者“不谦虚地炫耀自己的签名”(1986:7)。从而突显了两种文化及其语言体系之间的差异,并坚持将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阅读和写作行为,她把洛夫斯作为女同性恋的第三本书。
布罗萨德在这本书中从父权制圣体之外的立场出发建立了一条华而不实的语义链,构成了对女性写作意义的差异分析。(1986:8)戈达尔以文学评论家的身份,描述了前两本书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故事讲述和具象细节不再存在,布罗萨德正在寻找“女同性恋文本的轨迹”(同上:9)。她以“洛夫瑟”的翻译史为结尾,提到了她在阅读部分作品时所产生的“口头禅翻译”,以及她对文字游戏和鉴赏力的研究。她对布洛萨德的绘画理论的介绍和理论上的有形词是相似的,他们都是用与作者相似的语言表达的。德莱尔(1993)在加拿大的女权主义实践中指出,译者采用与作者相同的表达方式有助于与作者合作。同时它也说明了这个实验由于缺乏解释性语言而受阻。这个表述以其独特的方式去解释,很少有其他类似的语言存在。虽然戈达尔的学术引文(也包括论文、书评和会议文本)显然具有教育意义,但简短的译者脚注也能发挥类似的作用。
脚注在玛丽·戴利的德文翻译中被广泛使用,译者解释了她的德国读者无数次提到的美国文化和复杂的英语文字游戏。然而,译者通过用译者的笔记来标点文本的内容,使翻译更进一步。
例如,她意识到讲英语的女权主义学者在分析语言的父权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一直试图与德语相联系。当戴利分析代词系统时,它关注男性属性。她也干预了其他的方面,大概是因为戴利的文字看上去太模糊了。她为某些语义提供附加含义(同上:48)直接在文中对它们进行评论。维塞林克显然是个教育家,假设她的读者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听戴利的文章,他们可能需要一些指导。然而,在解释语言和文化问题时,这种教学方法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译者不能通过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来帮助他们。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误解,由于强调一些源文本根本没有语义或文化主体。就航空信件而言,例如,布罗萨德《拉莱特》的翻译(1985; 土耳其. 1988),原文中的文学共鸣是由译者识别的。其中包括标题、出版日期和页码都在脚注中列出。因此,在法文文本中,马拉尔姆的不清晰的主线和从罗兰德·巴特借用的内容被具体化为翻译中的书目顺序。译者也对法国文化参考文献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因此,虽然莱文和迈尔的对抗可能一定程度上与“女权主义时代”有关,一些译者所承担的解释功能也可以揭示文化迁移的局限性。有些材料不能照搬,而解释也许能像文本一样多地反映出译者的身份。
翻译修辞的修正
女性主义理论也导致了翻译术语的修订。这一修订版显然挑战了传统思维,例如如今经常被提及描述18世纪法国翻译的格言。这意味着如果翻译(和女人)是忠实的,他们很可能是丑陋的,如果他们是美丽的,他们很可能是不忠的。女性主义译者的自我及其目标对这种比较的评价导致了对翻译修辞的修订。
隐喻
在对过去几个世纪中用来描述翻译的隐喻的调查中,洛丽张伯伦(1988/1992)解释了翻译关系是如何在性别方面表达的以及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她的分析侧重于女性在语言和文化上的被压迫与翻译的贬值之间的密切联系。张伯伦认为,“不忠”等术语表达了对女性和翻译的贬低。20世纪的译者必须“控制文本”,以获得对其确认这种态度的控制。张伯伦主张用一种修辞的翻译来解构性别之间和文本等级之间的权力游戏。理想情况下,这将是一种将我们的思维从传统的负面理解和翻译方法中解放出来的方式。张伯伦的论点基于三个因素。首先,她展示了翻译的隐喻在历史上是如何在家庭中的权力关系中表达的,侧重于男性权威或家庭成员对女性行为的控制。因此,男性译者将自己塑造为文本纯洁的“守护者”,以免文字被玷污或玷污。他们以这种语言来守护这种监护权。这意味着文本(和女人)必须被控制,这样作者/丈夫才能确保他的后代-翻译或孩子是他的。其次,张伯伦展示了传统的翻译隐喻是如何接受和传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例如,圣经中提到强迫被奴役的妇女结婚前需要剃光头和修剪指甲,这就意味着一种女权主义思想所不能容忍的行为。第三,张伯伦展示了20世纪的理论家乔治·斯坦纳和SergeGavronsky如何利用男性性行为的语言和神话来描述翻译和俄狄浦斯情结,再次忽略了女性的参与和贡献,并使对他们的蔑视或暴力的言论永久化。
张伯伦对这些隐喻的列举和分析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她的结束语仍然是一种尝试性的论断。她仅限于引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潜在有用性,这些理论模糊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界限。
实现政治能见度
在加拿大,由于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更多以行动为导向的理论得到了阐述。例如,戈达尔认为女性翻译家篡改了原文,以及她们在生殖工作中的传统从属角色。她们“女性化”了文本,从女权主义者的原文中获得了这样做的权利,这为如何处理类似情况树立了榜样。她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翻译中表现出他们的创造性作用,正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传统上看不见的女性作品的力量的关注。
戈达尔的工作还有另一个维度。她抨击传统主流的重要女性文本翻译,抨击法国理论家伊瑞葛来和西克斯作品的英美版本。对于戈达尔,翻译“使用在目标语言的规范化系统中突出的行为模式和模式,将不同的转变成相同的”(1991:113)。换言之,翻译将Irigalayi的源文本整合到主导的“规范化”意识形态中,赋予意识形态意义,而不考虑女性主义在伊里加莱作品中的多重层次意义。这就产生了一个单一的文本,一个为单一信息(意义)而奋斗的文本,它可能很容易读懂,但实际上与女性主义理论家伊里加蕾的意图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西克斯作品的翻译则是在法国与西克斯合作制作和出版的,通过转移意义来促进和执行女权主义的意义生产。将文本转换成一种与法语原文一样奇怪的英语形式。在这种翻译策略的批判中,戈达尔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产生了两大特点。首先,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和写作被认为女性译者提供了保证,即没有任何文本是中立的或普遍有意义的,或者是“原创性”的。任何文本都带有它的生产者的标记,也是它产生的思想和文化背景的标志。此外,每个读者都会为文本添加自己的理解。因此,在有利于女性主义写作的语境和文化中工作的女性主义翻译家(作为女权主义读者和改写者)很可能产生与其时代相一致的政治作品。戈达尔将这一观点表述为:“翻译,在这一女性主义话语理论中,是生产而不是再生产”(1990:91)。在其他地方,她把女权主义翻译描述为“变革”,她把这个词称为“变革”。强调翻译工作,注重转换活动中意义的建构过程,是一种表现方式。(1990:90)
戈达尔认为,译者在女权主义时代工作,使他们的翻译在源文化中发挥原文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将文本移动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4952],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分裂句和假分裂句外文翻译资料
- 盖茨比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外文翻译资料
- 庞德诗歌中的美学与方法论价值外文翻译资料
- 功能对等理论观照下的《权力的游戏》中文字幕翻译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外文翻译资料
- 弹幕视频信息安全机制的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aboo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ual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外文翻译资料
- 目的论视角下的婴幼儿用品品牌翻译外文翻译资料
- 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外文翻译资料
- 《罗密欧与朱丽叶》对莎士比亚时间谜题的解决外文翻译资料